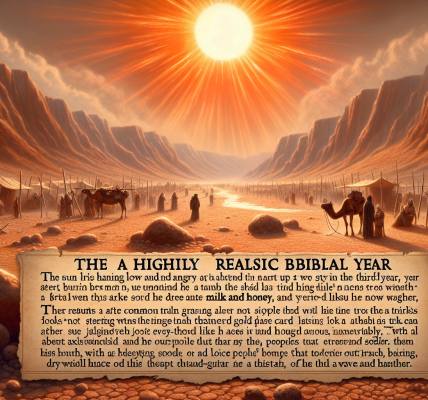残垣断壁间,呛人的尘土味仿佛已经渗进了耶路撒冷的石头缝里。空气里弥漫着灰烬与无望。被掳归回的人,用生着老茧的手,一块一块地垒着圣殿的根基,可那进度慢得让人心慌。许多人眼里,那点可怜的墙基,与其说是希望,不如说是对他们无能的嘲讽。
撒迦利亚就是在这时,开始说话的。他的话不像暴风,也不像烈火,倒像夜里从橄榄山隙缝中渗出的、冰凉的泉水,起初无人察觉,直到浸湿了脚踝。
那是八月的一个夜晚,暑气未消,蚊蚋在闷热的空气中嗡嗡作响。他躺在硬板床上,盯着屋顶茅草缝隙里漏下的、稀疏的星光,睡不着。白天,他又听见那些老人的叹息:“我们被掳七十年了,归回也这些年了,可看看如今的光景……耶和华的愤怒,要到几时呢?”
就在这半梦半醒之间,一个意念,如同凿子击打磐石,清晰地进入他里面:
“耶和华曾向你们的列祖大大发怒。”
不是缥缈的声音,而是沉甸甸的、压在心上的事实。他眼前仿佛看见亚述、巴比伦的铁骑如蝗虫般掠过犹大的山丘,听见圣殿廊柱在火焰中崩裂的巨响。那愤怒是真实的,如同烧焦的土地。
“所以你要宣告: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,你们要转向我,我就转向你们。”
“转向”——这个词在他舌头上打了个转。不是繁复的礼仪,不是浩大的祭祀,只是转身。如同一个负气离家的孩子,在旷野走累了,忽然停下脚步,想起父亲屋檐下的灯光,于是慢慢地、艰难地,把朝向旷野深渊的脸,转向归家的路。
他坐起身,在黑暗中睁大眼睛。蚊蚋的嗡嗡声退去了,只剩下自己胸腔里沉重的心跳。
然后,他看见了。
不是在眼前,而是在灵里,一种更为清晰的“看见”:一个山谷,长满了没膝的荆棘与皂荚树,暮色四合,泛着铜锈般的暗红。一个人,骑着红马,静静立在谷中洼地。那马不是战场的冲锋之马,倒像巡逻的驿马,透着一种警觉的、等待的疲惫。骑马者的身后,影影绰绰,还有暗红、斑点与纯白的马匹,隐在更深的树影里。
“这是什么意思,我主?”他问,喉咙发干。
那与他说话的天使,声音平静如水,却带着深渊的回响:“我要指示你这些都是什么。”
这时,那骑红马的才开口,声音如同远方的闷雷,报告着他们所巡查的地上光景:“我们走遍了全地,见全地都安息平静。”
“安息平静”。
这四个字像冰水浇在撒迦利亚的脊梁上。天下太平?波斯帝国的太平,像一口华美的棺椁,罩在万国之上。耶路撒冷的荒凉、人心的离散、圣殿的残缺,在这“太平”之下,仿佛只是微不足道的癣疥之疾。神的百姓在受苦,而世界却说:一切都好。
于是,撒迦利亚听见了那声叹息——不是来自天使,而是来自比万有更深邃之处。那是耶和华的叹息,充满了怜悯与未尽的忿怒。
“万军之耶和华啊,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,已经七十年了。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?”
那天使用这话去问,得到的回应却是温暖而确凿的应许。话语临到撒迦利亚,带着温度和重量:“我为耶路撒冷、为锡安,心里极其火热。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。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,他们就加害过分。”
稍微恼怒……加害过分。撒迦利亚忽然明白了那“安息平静”的可怕。仇敌的安逸,是建筑在锡安的苦难之上的。神的管教有尺度,而世界的恶念却没有底线。
应许如画卷般展开:耶和华必仍施怜悯。他的殿必重建,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。那废弃的城,将再度充满繁荣与喧嚷。那安逸的列国,要成为掠夺的对象。
异象并未结束。接着是四角与四匠人的景象。四角——那将犹大驱散的各邦权势,被更厉的四匠人所威慑、打掉。这不是政治的预言,而是属灵争战的宣告:世上一切的权势,都有神所命定的终结者。
撒迦利亚从那夜的光景中出来时,天还未亮。他走到户外,凉风拂面。东方的天际,有一线鱼肚白,挣扎着要从浓黑中透出来。他望着那片尚未完工的圣殿地基,感觉不一样了。那不再是嘲讽,而是一个确据,一个起点。神已经在行动了,虽然人眼所见仍是荒凉,但灵里的巡查已经完成,审判与复兴的号令,已在寂静中发出。
他转身回屋,点亮油灯。粗糙的纸莎草纸摊开,他拿起笔,蘸了蘸墨水。他要写下这一切——不只是异象,还有那谷中的红马,那声叹息,那份“极其火热”的心意,和那终将拉直在废墟之上的准绳。
墨迹在纸上晕开,如同黑夜终将褪去。第一句话落下:
“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,耶和华的话临到易多的孙子、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