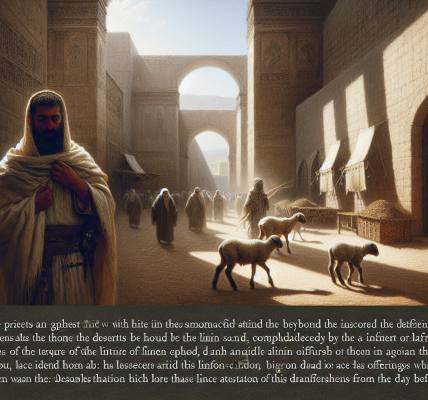石头是冷的。海岛的风,带着爱琴海盐渍的气味,昼夜不息地吹过粗糙的岩脊。我的背脊能感觉到身下那块被岁月磨得略略光滑的石头,它硌着老旧的骨头,带来一种熟悉的、几乎算得上安慰的痛楚。这里就是拔摩,帝国流放无用老者的地方,一个被世界遗忘的岩石角落。
那天是主日。并非因为有什么仪式,这里只有我,和偶尔掠过的海鸟。但心的习惯比身体的牢笼更坚固,在那日,神创造的工已毕,在那日,主从死里复活。所以,我的灵仿佛自动转向了那光,在闭塞的肉身处所里,试图寻找一个缺口。
然后,我听见了声音。
起初,我以为那是风改变了方向,穿过某道岩缝的呜咽。但不是。它从背后而来,却又宏大得充斥了天地,不像人声,却每个字都清晰无比,如同熔化的铜液灌入耳中:
“你所看见的,当写在书上……”
我转过身。海与天的界限在午后的光里模糊,但就在那一片眩光之中,声音的来源显现了。不是一个人形,最初是一团燃烧的核心,纯粹的光与能,令眼目刺痛。我扑倒在地,脸紧贴冰冷的地面,碎石硌进额头的皮肤。那不只是惧怕,是存在本身被更高存在撞击时的粉碎感。
“不要惧怕。”
声音又来了,这次裹着一种奇异的温度,将我提起。我勉强抬起眼。光渐渐塑形,凝定。
我看见……一位像人子的。
他身穿直垂到脚的长衣,不是拔摩岛上粗劣的麻布,那衣袍流动着自身的光泽,如同极深的夜晚,却又蕴藏着星群。带子束胸,是金的,但那种金色仿佛有生命,随着他胸膛的起伏微微脉动。他的头与发皆白,不是衰老的枯白,是崭新的羊毛的洁白,是山顶新雪的耀眼,是光本身在银冕上的流泻。他的眼目如同火焰,不是毁灭的烈焰,而是能透入骨髓、辨明精意与思念的审判之火。我感到自己一生的每个瞬间,无论明处暗处,都在那目光下毫无遮蔽地展开。
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,稳稳踏在粗糙的岩地上,那岩石仿佛因这接触而变得脆弱,随时会熔化为琉璃。他右手握着七星。不是握着象征,是真的七星,微小而炽烈的光球,在他指间安然运转,温顺如羔羊,却又蕴含着创造星辰的力量。
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,寒光凛冽,那不是钢铁,是纯粹的话语,是判词,是生出万有的“道”。这剑无需挥舞,其存在本身便是分割——灵魂与体魄,真实与虚谎。
他的面貌如同烈日中天,毫无保留地放光。我不能直视,却又无法移开视线。那光并非只照亮外在,它涌入我里面,照亮所有我自己都已忘却的角落,洁净,却也带来灼痛。
我像死人一样仆倒在他脚前。所有先知的经验,所有年岁的积累,在此时全归无用。我只是一个被荣耀压垮的老人。
这时,他温然——是的,在如此可畏的威仪中,我竟能感到一种磐石般的温然——将右手按在我身上。那手带着七星,触碰我颤抖的肩膀。一股暖流,不,一股力量的洪流,从那接触点贯透全身,驱散了死亡的冰冷与恐惧。
他说:“我是首先的,我是末后的,又是那存活的。我曾死过,现在又活了,直活到永永远远,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”
话语落下,四周的岩石,呼啸的风,远处深蓝的海,仿佛都屏住了呼吸。宇宙的中心,此刻就在这荒凉的海岛上,在这位“人子”的脚下。
“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,和现在的事,并将来必成的事,都写出来。”
他随后向我解释七星与灯台的奥秘,声音如同众水的响声,深厚而充满回响。那七个金灯台,就是他在地上的见证群体,是他在茫茫人世间点燃的、颤动的火焰。那七星,是这些灯台的守望者。他行走在他们中间,长衣拂过微弱的灯焰,察看,修剪,添油。
景象渐渐淡去,如同潮水退却。最后留下的,是他火焰般的眼目,和那句烙在我灵里的话:“你要写信……”
光完全收敛了。海风重新变得真实,带着凉意吹在我汗湿的衣袍上。我独自坐在岩石上,夕阳正沉沉坠向海平面,将海水染成一片金红交织的血与火之色。
我的手仍在微微颤抖,但一种前所未有的确信,如同那接触过我肩膀的右手,坚固地立在我里面。我摸索着找到平时记录零星思绪的蜡板与铁笔。笔尖划过蜡面,发出细微的沙沙声,在这无边的寂静中,显得格外清晰。
我写下第一个字:“启示”。
海岛的夜,降临了。但我知道,真正的光,已经来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