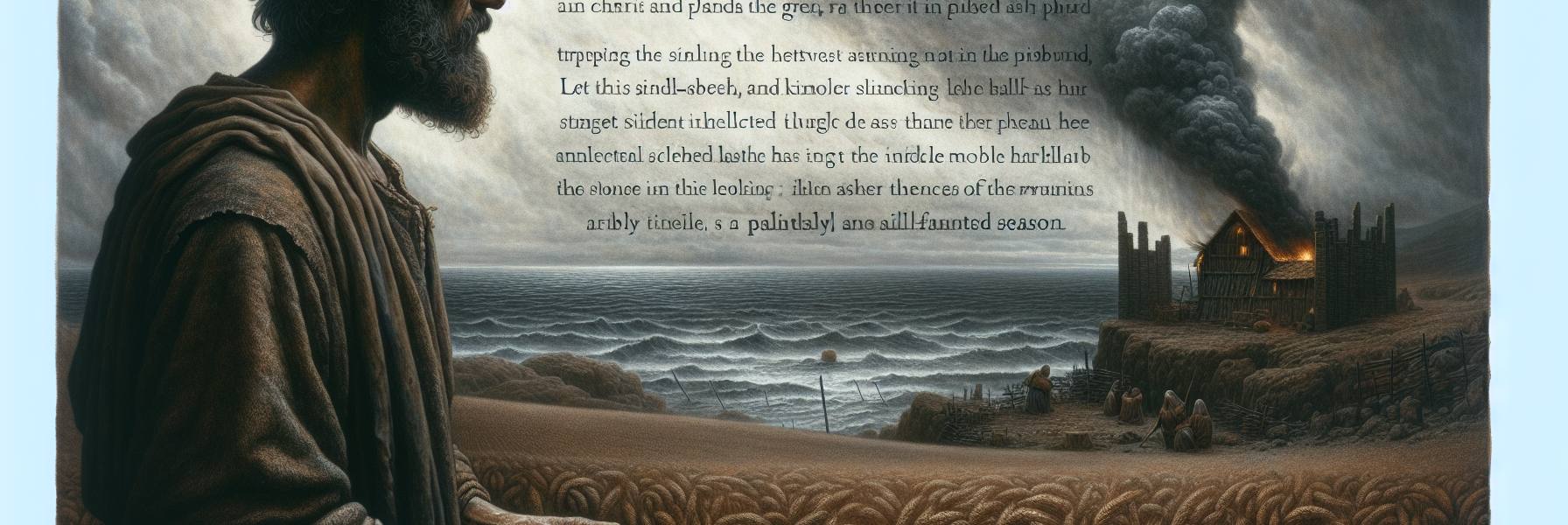城墙的影子斜斜地压在卵石路上,将雅罗城分割成明暗两半。亚比煞推开门时,正看见她丈夫西拉坐在橄榄木凳上,对着空墙发怔。他的手搁在膝盖上,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,像河边被水浸透的石头。
早晨的消息来得猝不及防。从叙利亚来的商队指来口信,说有一艘船在奇里乞亚沿海遇到了风浪,货物尽数沉没。那船上有西拉投进去的大半家当——本地的细麻布,还有两箱没药。如今只剩下一句轻飘飘的“沉了”,飘过沙漠与山岭,落在他们这间临街的屋子里,重得让人直不起腰。
西拉没哭,也没嚷。他一整天就那样坐着,从日头初升坐到影子拉长。亚比煞把凉了的饼子热过两回,汤在陶锅里凝起一层油脂。她终于挨着他坐下,肩膀轻轻碰着他的肩膀。
“你想说话吗?”她问。
西拉喉咙里滚过一声响动,像被堵住的溪流。“说什么呢?说我们如何从头开始?说我怎么这样糊涂,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破篮子里?”他摇摇头,目光仍黏在墙上某块斑驳的痕迹上,“我是个傻瓜,亚比煞。一个十足的、该被嘲笑的傻瓜。”
亚比煞没反驳,只是把手覆在他手背上。他的手很冷。她想起新婚那年春天,他们一起栽下的葡萄藤。头一年冬天特别寒,雪埋了土墩,西拉担心藤子冻死,每天去探看。后来藤子活了,抽了新绿,他笑得像个孩子。那时他说,生命比我们想的坚韧。
“你还记得老以利户的话吗?”她缓缓地说,“就是那位总在集市角落讲律法的长者。他说,试炼来临的时候,要看作是一件……一件值得欣喜的事?”
西拉终于转过脸来,眼神里有疲惫,也有不解的微火。“欣喜?我的船沉在海里,我半生的积蓄泡了盐水,你要我欣喜?”他声音不高,却像绷紧的弓弦。
“不是为损失欣喜。”亚比煞从怀里摸出一块磨得光滑的小石片,上面刻着些希伯来字母,是西拉早年练字时留下的。“是为这试炼能带来的……耐力。”她指着一个词,“他说,耐力需要经过完整的炼制,人才会健全,什么都不缺。”
风从门缝钻进来,吹动墙角的沙粒。西拉沉默了很久,久到亚比煞以为他不会再开口。然后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,那气息里积压了一整天的郁结似乎松动了一丝。“健全?我现在只觉得残缺,像破了的瓦罐。”
“破了的瓦罐,”亚比煞接得很快,“若是交给巧手的匠人,能用金丝缀补,变得比原来更珍贵。”她顿了顿,“我不是说我们的难处算不得什么。它是重的,非常重。但或许……或许它也是个机会,让我们看看自己信心的成色究竟如何。就像验金子的火。”
那天夜里,西拉梦见海。不是吞噬他货物的狂暴的海,而是更早以前,他随父亲去约帕时见过的、拂晓时分平静无波的海面,泛着一种介于铁灰与淡金之间的光。他在梦里听见一个声音,不高,却穿透涛声:“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,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、也不斥责人的神……”
他醒来时,天还没亮。亚比煞在他身边睡得很沉,呼吸轻缓。他轻轻起身,走到小小的内院。星星还钉在天鹅绒似的天上,清冷的光照着院角那株葡萄藤。它今年结了果,不多,但颗粒饱满。
西拉在井边坐下,不是祷告——至少不是那种字句分明的祷告。更像是一种呆坐,一种把整个摊开的、不知所措的自己摆在寂静与星空之下的裸露。他没有求神让货物回来,那太不真实。他只是坐在那里,让那股从昨日早晨就梗在胸口的硬块,慢慢地、痛楚地融化。然后一个念头,像初生的藤蔓尖,悄悄探出来:或许我该去求的,不是失而复得,而是如何面对这“失”。
这念头本身,让他感到一丝奇异的松动。
日子像雅罗城外的沙子,一层层覆盖上来。西拉开始重新接些零散的染布活计,那是他早年的手艺。手指浸在靛蓝与茜草红的染缸里,一整天下来,掌心的纹路都渗着颜色。劳累是实的,腰背的酸痛是实的,但每晚清点那点微薄收入时,一种缓慢生长的踏实感,也是实的。
有一天,他染坏了一匹布。颜色染花了,深一块浅一块,客户定然不要。西拉盯着那匹布,一股熟悉的焦躁涌上来,几乎要将他淹没。他想把那布扔了,想踢翻染缸。但就在他弯腰去抓那匹布时,亚比煞的话和梦里的声音重叠着响起来:“……只要凭信心求,一点不疑惑……”
他停住了。疑惑?他此刻充满疑惑。疑惑自己是否还能翻身,疑惑这苦日子有没有尽头。但他看着自己染花的、颤抖的手,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:疑惑的对面,不是全然的确定,而是即便在不确定中,依然选择伸手去求的那一点点倔强的盼望。
他留下了那匹布。后来,他把它裁开,染花的部分拼接起来,做成了一种独特纹样的垫子,反而在集市上卖出了不错的价钱。这不是神迹,没有天使歌唱,只是一个染匠在无奈中挤出来的一点灵光。但西拉在数那些钱币时,心里想起“厚赐与众人、也不斥责人的神”这句话,忽然觉得,智慧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启示,有时就是染坏了一匹布之后,没有把它扔掉的那个停顿。
秋天,葡萄熟了。西拉和亚比煞一起采摘,紫黑的果实沉甸甸地压弯了藤蔓。他们酿了新酒,也留了一些晒成葡萄干。傍晚,他们坐在院子里,分享一小碗果实。西拉嚼着葡萄干,甜味里带着阳光和时光的味道。
“我还是会想起那艘船,”他说,声音很平静,“想起那些没药沉在黑暗的海底。但那种想起,不再像刀子割肉了。它变成了一种……记忆的褶皱。”
亚比煞看着他。他脸上的纹路深了些,但眼神不再涣散,像经过搅动又重归清澈的水。“老以利户还说,”她微笑道,“那经得起试炼的人,会得到生命的冠冕。我从前总想象那是金子做的,发光耀眼。现在觉得,那冠冕或许就是像今晚这样的平安。它不耀眼,但结实,能戴得住。”
西拉点点头。他望向城墙之外更辽阔的夜空。试炼没有让他变得富有,也没有让他变得聪明绝顶。但它像一趟被迫的远行,让他走了一条从未想走的、崎岖的路,反而看见了不一样的风景。他依然是那个会犯错、会忧虑的西拉,但他的里面,有些东西被炼制过了,像陶器经过窑火,依然有裂缝的阴影,却也多了一层坚硬的、哑光的釉质。
风起了,带着凉意。他们收拾碗碟进屋。门关上之前,西拉又回头望了一眼星空。海上或许仍有风浪,人生也必然还有试炼,但此刻,在这小小的、充满葡萄甜香的院子里,他感到一种奇异的、扎实的完整。那冠冕无声,却已落在他生出了白发的头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