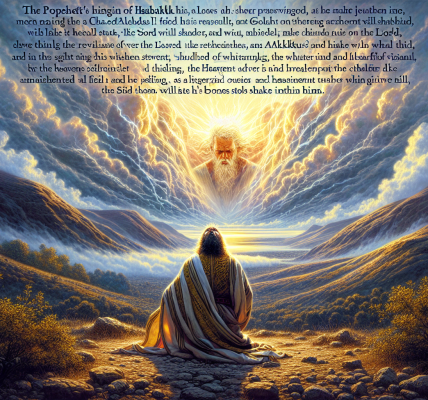曠野的風,已經吹了三個月。自從他們離開埃及,這風就沒有停過,帶著細沙,鑽進每一個帳篷的縫隙,也鑽進人心裡,留下一种粗糙的、不安的窸窣聲。白天,雲柱在前頭飄動,潔白得令人不敢直視;夜裡,火柱燃燒著,把起伏的沙丘照成一片流淌的銅海。人們跟著,但心裡空落落的,像背著一隻沒有壓艙石的船。
然後,隊伍停在了西奈的山腳下。那山不同於周遭土黃的曠野,它裸露著深灰色的巖骨,陡峭地插向天空,山頂終日裹在一團濃厚的、不動的霧氣裡,那不是雲,更像一塊沉甸甸的毛織幔子。摩西上了山,一去就是許多日。百姓在下面等著,等待滋生猜測,猜測又釀出隱隱的焦躁。他們需要一點什麼,一點比嗎哪和鵪鶉更實在的東西,一點能抓住的,能明白的,能告訴他們“為何在此”的東西。
那天清晨,空氣凝滯得反常。連慣常的風也住了,營地裡只聽見羊群偶爾的咩叫和孩子壓低的啼哭。忽然,沒有預兆地,一聲沉悶的巨響從地底滾過,像有巨大的石輪碾過深淵。人們驚惶地衝出帳篷,看見西奈全山冒煙——不是山火那種跳躍的赤紅,而是厚重的、墨黑的煙,如同燒著了世上所有的煤炭。煙柱筆直地升騰,山卻在劇烈地顫動,彷彿有什麼活物要從那巖石的囚籠裡掙脫出來。接著,雷聲來了,不是天邊的悶雷,而是緊貼著頭皮炸開的霹靂,一聲接著一聲,沒有間隙,震得人五臟六腑都在共鳴。閃電在濃煙中劈開慘白的光,一剎那照亮整座猙獰的山體,下一刻又讓它陷入更深的黑暗。
角聲響起。那聲音極其鋒利,極其悠長,不像出自任何牧人的羊角。它越吹越響,穿透雷鳴,直刺入人的骨髓裡,帶來一種冰冷的、幾乎要嘔吐的恐懼。全營的百姓都在發抖,不由自主地戰慄,從老人到吃奶的嬰孩。他們擠在一起,望向那山,山在烈焰與濃煙中彷彿正在熔化,又彷彿正在凝固成一種更為可怕的形態。
摩西從人群中走出,臉色在閃電的映照下顯得灰白而堅定。他沒有說話,只是用手勢安撫著躁動的人群,然後轉身,一步一步走向那咆哮的山腳。百姓看著他的背影沒入翻滾的煙氣邊緣,覺得他彷彿正走向世界的盡頭。
聲音就是在那時傳來的。不是通過耳朵,而是直接響在胸膛裡,響在靈魂最深處那片空曠之地。那聲音無法用人間的詞彙形容,它包含著雷霆的威嚴,也包含著創造諸世界之初那第一縷光的溫柔;它震碎一切傲慢,同時又托住一切將墜的脆弱。
“我是耶和華你的神,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。”
話語落下,如同第一塊基石沉入洪荒的混沌。時間彷彿停滯了。曠野的喧囂——風聲、雷鳴、角聲、山的震動——並沒有消失,卻突然退到了極遠的後台,成為這聲音的襯底。這句話本身成了一個宇宙,浩瀚而清晰。它不是一個抽象的宣告,而是一個帶著溫度、帶著行動、帶著裂開紅海之記憶的宣告。從為奴之家……每個人都感到自己腳踝上那看不見的、曾被埃及的泥磚磨破的傷痕,隱隱作痛。
接著,話語如鑿刻星辰般繼續:
“除了我以外,你不可有別的神。”
山巒似乎在他的宣告中顯得更為永恆。那不僅是一條禁令,那是一道邊界,將無限的忠誠劃歸於一處。漂泊的靈魂第一次有了不可移動的錨點。
“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……”
閃電照亮人們腰間偷偷藏著的、從埃及帶出來的小小的河馬神像,或是用銀子捶打的月牙飾品。話語如光,照見那些暗中的依賴與懼怕,並將其剝離。
“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……”
那些在艱難中輕易脫口的抱怨,那些將神之名與俗世瑣事輕率相連的習慣,此刻在話語的重量下,顯得分外輕浮且危險。
“當記念安息日,守為聖日。”
在無休止的奔波與生存壓力中,這句話像一道溫柔的命令,劃出時間的聖所。勞碌的身體與焦灼的心靈,被許諾了一處避難所。
“當孝敬父母……”
家族帳篷裡,年邁父母昏花的眼中閃過一絲難以置信的亮光。延續,應許,秩序,從這最基本的紐帶開始。
“不可殺人。”
“不可姦淫。”
“不可偷盜。”
“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。”
“不可貪戀……”
每一句,都像一柄精準的雕刻刀,在混沌的人群中劃出清晰的人形輪廓。關乎生命,關乎忠誠,關乎財產,關乎言語,最後,直指內心那最隱秘的動念。這不是一系列繁瑣的規條,而是一幅完整生活的藍圖,從對至高者的關係,到對鄰舍的關係,再到對自我的管束。它們彼此勾連,形成一個約的框架。
話語說完了。餘音還在諸山之間迴盪,與漸漸平息的雷聲混在一處。那令人窒息的、直接的臨在感,如同潮水般從營地退去。濃煙開始消散,火燄逐漸熄滅,角聲也已止息。西奈山重新顯露出它深灰色的巖石,在正午慘白的日光下,沉默而威嚴。
百姓仍站在原地,一動不動。恐懼並未隨著聲音消失而消失,它沉澱了下來,化作一種冰冷的、貼著皮膚的敬畏。他們臉上的表情是空白的,因為承受了過於沉重的東西。他們對摩西說:“求你和我們說話,我們必聽;不要神和我們說話,恐怕我們死亡。”
摩西看著他們驚魂未定的臉,心裡明白,這恐懼是好的,是認識的起頭。他轉向那山,煙靄仍未散盡的山巔。約已經賜下,那以雷電與火焰為筆,刻在民族靈魂上的十句話。這不是終點,而是立約關係的開始。路還長,曠野依然無邊無際,但從此,他們行走其間時,頭上有了蒼穹,腳下有了道路。
他整了整衣衫,邁步再次向山上走去。百姓遠遠望著,這一次,他們眼中除了畏懼,似乎也多了一點別的東西——一種模糊的、剛剛萌芽的、關於秩序與盼望的認知。風又開始吹了,掠過靜默的營地,帶著西奈山石燼火的微溫,也帶著遠方應許之地那不可見的、荊棘與蜜的氣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