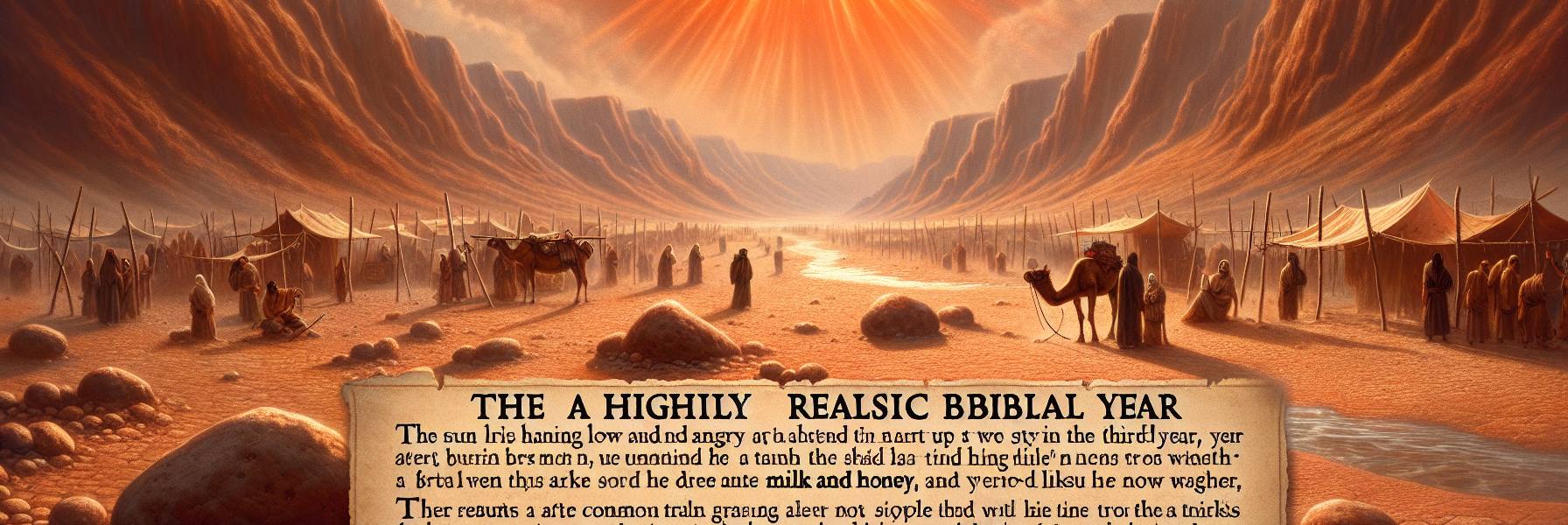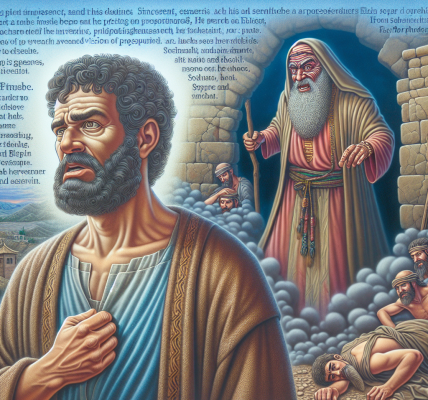雨已经停了三天,但河谷里的石头还湿漉漉的,泛着深色的水光。亚比押把羊群赶到溪边时,太阳才刚爬上东边的山脊。他是个老牧人,指节粗大,脸颊被多年的风日蚀出沟壑。羊群熟悉他的哨声,慢吞吞地散开,低头寻觅石缝间新冒头的草尖。
不远处的基列城却醒得更早。炊烟从泥砖房的平顶升起,混着烤饼和橄榄油的味道。近来城里总有些不一样的动静——不是节期,也不是集市的日子,但总有三五成群的人聚在城门口那棵大橡树下,低声说着什么,眼睛闪着光。
亚比押的孙子以拉跑来时,喘着气,手里攥着一块用细麻布包着的东西。“爷爷,”少年人的声音又急又亮,“马但家的儿子从摩押回来了,带着这个。”
麻布掀开,是一尊手掌大小的像,光滑的黑色石头雕成,人形,却生着牛角和翅膀。雕工很细,翅膀上的羽毛一根根清晰可辨。亚比押接过来,掂了掂,石头冰凉。他没说话,只是用拇指摩挲过那对弯曲的角。
“他们说这是新的神明,”以拉的眼睛睁得很大,“比我们的耶和华更灵验。摩押那边干旱了三年,他们献祭给这神,雨水就来了。迦南的商队也说……”
“说什么。”亚比押的声音不高,却让少年停住了。
“说我们的神严厉,要求太多。而这神……赐福慷慨。”
溪水潺潺地流。一只母羊抬起头,嘴角还挂着草茎。亚比押望着对岸的城墙,想起许多年前他父亲的话:石头会朽坏,河水会改道,但立约的话立在天上,不落在地上。
那天傍晚,城里果然聚起了更多人。从摩押回来的那人叫示利米雅,很年轻,穿一件镶红边的外袍,说话时手势翻飞。他站在橡树下,身边已经围了二三十人。亚比押站在人群边缘,背靠着粗糙的树干。
“我不是说要废弃我们祖辈的神,”示利米雅的声音清亮,像山涧的水,“但各位想想,过红海是哪一代人的事?四十年旷野,又是哪一代人的事?我们如今住在这城裡,种葡萄,养儿女,我们需要的是能让田产丰饶、让牲畜繁殖的神。这尊巴力像——”他举起那黑色的小像,“它在摩押显过大神迹。我们为什么不能也求它的庇护?多一个神,多一条路。”
有人点头。那是织布匠的儿子,去年他的羊群染了疫病,死了一大半。又有人附和,是城门边卖陶器的寡妇,她丈夫死在非利士人的掠袭中。亚比押看见他们脸上的神情——那种急于抓住什么的渴望,像干渴的人看见海市蜃楼里的水。
一个白发老人颤巍巍地开口:“示利米雅,你小时候我也抱过你。律法书上写得明白……”
“律法书!”示利米雅打断他,语气依然温和,甚至带着惋惜,“老人家,律法是好的。但我们活在当下啊。摩西上山领诫命时,我们的祖先在山下铸金牛犊,不也是因为等得心慌,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凭据吗?人心就是这样。”
月亮渐渐升起来,惨白的一弯。亚比押转身离开,踩着自己的影子往回走。夜风里有野薄荷的苦香。
之后几天,事情悄悄蔓延。先是有人家在后院的无花果树下垒了个小石坛,接着是铁匠铺的角落里出现了同样的黑石像。示利米雅常在黄昏时讲说,声音越来越自信。他引用古老的诗句,却把意思拧转;说起祖先的故事,却省略关键的段落。亚比押远远听过两次,心里像压着块湿泥。
第七天,示利米雅宣布要在月圆之夜,在城外山谷的平地上举行第一次正式的祭礼。“不强迫任何人,”他说,“但愿意得新福分的,可以带一只羊羔来。我们不用燔祭,只取血洒在坛前,肉大家分吃,像一家人。”
那夜亚比押没睡。他坐在土屋门口,望着满天密密的星子。孙子以拉翻来覆去,终于小声问:“爷爷,我们不去吗?以撒家、约珥家都说要去。连……连拿单长老好像也没说不让。”
亚比押很久没回答。他想起申命记里那些被羊皮卷磨得发亮的话,一句一句,沉甸甸的。不是石头的重量,是另一种更重的东西。
月圆之夜,山谷里果然燃起了篝火。去了约莫三十多人,多半是年轻人。示利米雅站在临时搭起的土坛前,坛上立着那尊黑石像。他们宰了羊羔,血渗进干裂的土里。肉香混着松脂燃烧的味道,飘得很远。有人在唱歌,不是往常献给耶和华的诗歌,而是轻快的、带着异域调子的曲子。
亚比押没靠近。他站在西侧的山坡上,能看见全部,自己却隐在阴影里。他认出好几个熟悉的身影:帮他补过羊圈的木匠,常送他新鲜乳酪的妇人,还有孙子以拉最要好的玩伴。火光在他们脸上跳跃,表情恍惚而热切。
突然,示利米雅举起双手,声音在山谷里回荡:“看哪!这坛前的火格外旺!这是接纳的记号!”人群发出欢呼。但亚比押眯起眼——他看清了,是示利米雅的一个同伴,悄悄从侧面添了浸过油的松枝。
第二天,亚比押去找了拿单长老。老人坐在自家院子里的葡萄架下,眼窝深陷,像是一夜未眠。
“你都看见了。”拿单说,不是问句。
“看见了。”
“你怎么想。”
亚比押从怀里掏出那卷常读的申命记,皮子边缘已经磨得发白。他没翻开,只是平放在石桌上。“十三章。‘你中间若有先知……显神迹奇事……说: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吧……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,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、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……你便要将他治死。’”
念到最后几个字,他的声音干涩。葡萄叶子沙沙响。
拿单长长地叹气:“示利米雅是我侄儿。他父亲……我兄弟,战死在基色。这孩子小时候总缠着我问,为什么我们的神让好人死掉。”
“所以就该转向石头雕的神吗?”亚比押问,声音很累。
沉默了很久。一只蜜蜂嗡嗡地撞进葡萄花里。
“律法不只给我们权利,”拿单终于说,每个字都像从石头里凿出来的,“也给我们重担。这重担就是:当亲近的人走迷了路,当那路看起来繁花似锦,我们仍要认得那是迷途。爱有时候长着一张严厉的脸。”
他们又找了其他几位长老。争论、叹息、沉默。有人掉泪——示利米雅的姨母,一直攥着衣角。但皮卷上的字黑黢黢的,不因人的忧愁褪色。
三天后,全城被召到城门口。示利米雅被带出来时,没有绑绳索,脸上还带着困惑。“叔叔?”他看着拿单。
拿单不看他,面向众人,背脊挺得笔直,声音却像裂开的陶器:“我们查证了。那些神迹是人的手法,那些应许是沙土垒的台。他引你们去的,不是活水的泉源,是漏水的池子。按我们与神所立的约,这事的结局已写在律法书中。”
示利米雅的脸一点点白下去。他忽然喊起来:“我只是想让大家过得好一点!有错吗?律法!律法比活生生的人还要紧吗?”
没人回答。只有风吹过橡树叶子,哗啦啦一片响。
亚比押走上前。他手里没有石头,也没有武器。他只是站在侄子辈的年轻人面前,看着那双曾经清澈、如今烧着不服和委屈的眼睛。
“示利米雅,”老牧人的声音沙哑,“若今日我们为你破一次例,明日就有人为别的事再破例。一代人,两代人,等到我们的孩子问你:律法究竟算什么?你怎么答?说它可以按我们的方便修改吗?那约就不再是约,成了可撕可改的羊皮纸。到那时,我们和周围列国还有什么分别?我们凭什么存留在这地上?”
他停住,喘了口气,像走了很远的山路。
“你说的对,律法严厉。但你知道吗?它首先是对我们自己严厉。因为它信我们能承受这严厉,配得上这严厉。它不把我们当需要哄骗的孩子,它当我们是立约的大人。”
行刑的时候,亚比押要求亲手做。不是出于恨——他眼里没有恨,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哀伤。石头举起落下之间,他听见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碎掉了,脆生生的,像冬天的冰。
事后,人群默默散去。亚比押留在最后,和拿单一起,把示利米雅和那尊黑石像埋在无人记念的山谷阴面,不起坟堆,不立标记。土填平后,拿单忽然站不稳,亚比押扶住他,发觉老人在发抖。
“我兄弟只剩这根苗。”拿单的声音轻得像耳语。
“我知道。”
“我们做对了吗?”
亚比押望向西沉的太阳,巨大的日轮正坠入远山背后,把云烧成紫红的灰烬。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了实话,“我只知道,若不做,今夜我无法面对这星空,也无法面对子孙将来要住的那片土地。”
他们摸黑下山。亚比押的脚踩到一块松动的石头,踉跄了一下。以拉从后面扶住他。少年人的手很稳,沉默了一路,此时忽然开口:
“爷爷。”
“嗯。”
“我会记住今天。”
亚比押侧过脸,看见孙子眼里映着最后的天光,清澈,却有了重量。他没说“好”或“不好”,只是把粗糙的手掌按在少年肩上,很重地按了一下。
夜里,羊群在圈中安歇。亚比押坐在门槛上, again 望着星空。那律法的文字在他心里翻腾,不再只是羊皮卷上的墨迹,它们沾了血,沾了泪,沉甸甸地坠在生命的根基处。旷野的风吹过四十年,吹过约旦河,如今吹在他脸上,还是那么硬,那么不容分说。
他忽然很累,累得想就此睡去,不再醒来。但东方天际,最早的那颗晨星已经亮起来了,淡淡的,坚定的,像一句永不更改的应许,悬在万物之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