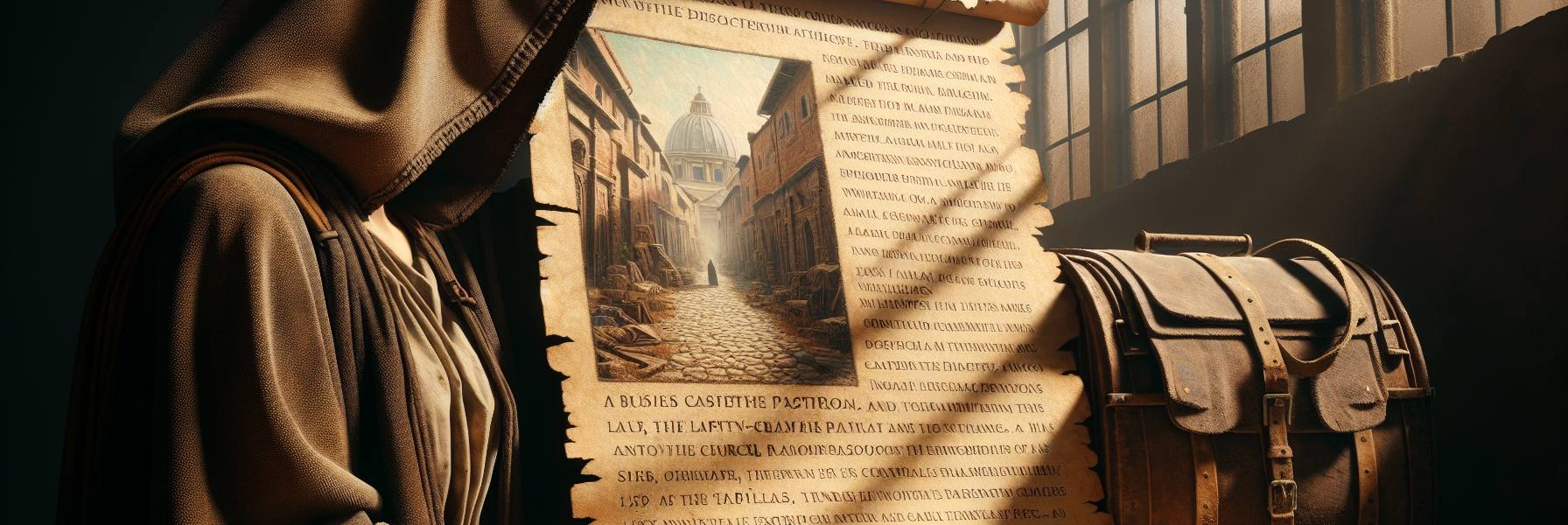窗外的罗马城正浸在将暮未暮的光里,尘埃在斜阳中浮动,像极细的金粉。我,特尔提,搁下笔,揉了揉酸胀的手腕。羊皮纸上墨迹已干,是老师保罗口述的最后一句话。但我的心里却翻腾着,那些名字,一个接一个,从他唇间流淌出来,仿佛不是问候,而是一幅用活生生的人绘成的圣徒相谱。
我想起昨天的情景。腓比来了,从坚革里来,风尘仆仆。她走进我们这间简陋的寓所时,不是昂首阔步的,而是带着一种沉静的疲惫,肩上的斗篷边角还沾着海盐的痕迹。她递上那封荐书时,手并不十分光滑,那是常年在事务中操劳的手。保罗接过,没有马上看,却先为她端了一碗清水。“姊妹,你在教会里素来帮助许多人,也帮助过我。”他说这话时,声音很轻,像在陈述一个再自然不过的事实,而非褒奖。腓比低下头喝水,我看见她眼角有细密的纹路,那是笑得多,或许也愁得多留下的。她不是传说中的人物,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,带着一路的尘土与信念,坐在了我们中间。
于是,随着保罗的口述,那些人便从记忆里、从传闻中活了过来。我写着“又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”,眼前就浮现出那对夫妻的帐篷作坊,空气里满是皮革与帆布的气味。亚居拉的手指粗壮,打结绷线又快又稳;百基拉说话时,眼睛总是先笑,然后才轮到嘴角。他们为了保罗的性命,连自己的颈项也置之度外——这话保罗说得平静,我笔尖却一顿,墨点差点晕开。那是什么样的情谊?不是轰轰烈烈的传奇,恐怕是某个深夜急促的敲门声,是慌乱中卷起的工具,是黑暗中默默引路的身影,是之后许多年绝口不提的沉默。
还有“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”。保罗念到这名字时,停顿了一下,仿佛在咀嚼某种很深的感情。他说他是亚西亚归基督初结的果子。初熟的果子……我想象那或许是个羞涩而坚定的年轻人,在众人还疑惑观望时,第一个走了出来,脸上带着懵懂却决绝的光。他的信,是最初的那一粒芥菜种,如今已长成一片荫凉。
一个个名字,带着他们的故事,嵌进了这信的字里行间。“为主劳苦”的马利亚,“与我一同坐监的”安多尼古和犹尼亚——后者竟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?保罗提到时,语气里有一种难得的、近乎骄傲的确认。他特意要问“在家庭教会中”的各位圣徒安,那“家庭教会”几个字,让我想起罗马城里那些并不起眼的房屋。或许是一处带天井的寻常宅院,傍晚时分,信徒们悄悄聚拢,没有宏伟的殿堂,只有低语的祷告、掰开的饼、传递的杯,还有彼此眼中映照的灯火。那危险而珍贵的聚集,才是教会最初的心跳。
信快结尾时,保罗的语气变得格外恳切,甚至急切。他提醒要防备那些“背乎所学之道”的人,那些“用花言巧语诱惑老实人”的。他说这些话时,眉头紧锁,不是出于愤怒,更像是一种深切的忧虑,仿佛看见无形的裂痕正在他所珍爱的这群人中间蔓延。最后,他归回那最初的奥秘:“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,如今显明出来,藉众先知的书指示万民,使他们信服真道。”念到“信服真道”时,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仿佛这便是这一切问候、提醒、劝勉与劳苦的最终归宿。
我写完了。最后的颂赞墨迹未干:“愿荣耀,藉着耶稣基督,归与独一全智的神,直到永远。阿们。”
屋里已经完全暗了下来。我没有立刻点灯,就坐在渐浓的暮色里。手里这卷信,忽然变得很重。它不再是字句,它是百基拉与亚居拉帐篷里的针线,是腓比渡海时打湿的衣襟,是特里非拿、彼息氏那些老姊妹在病榻前依然忙碌的双手,是犹利亚、尼利亚姐妹与那些无名圣徒在逼迫阴影下依然交换的平安吻。它是一个巨大的、看不见的网,用血肉之躯与坚韧信心织成,从耶路撒冷到罗马,从犹太会堂到外邦人的家。
而这网的中心,不是权力,不是律法,乃是一个名字:耶稣基督。他们因这名而活,也为这名相聚,甚至可能为这名而死。保罗问候他们,如同点数战场归来后散落在各处的战友,他知道每一道伤痕,记得每一张面孔。
我轻轻卷起羊皮纸,用细带系好。窗外,罗马的灯火次第亮起,帝国的喧嚣隐约传来。但在这间小小斗室里,却仿佛回荡着一片更浩大、更安静的嘈杂——那是无数脚步走向彼此、无数问候穿越关山、无数平凡生命被一个不平凡的恩典所连接的声音。这封信,即将被腓比带走,踏上回程。它本身,也成了这巨大网络中新的一根丝线。
夜深了。我终于点燃陶灯,一点昏黄的光晕开。我知道,明天这信就要送出去,而它所承载的那个看不见的国度,将继续在可见的裂隙与劳苦中,默默生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