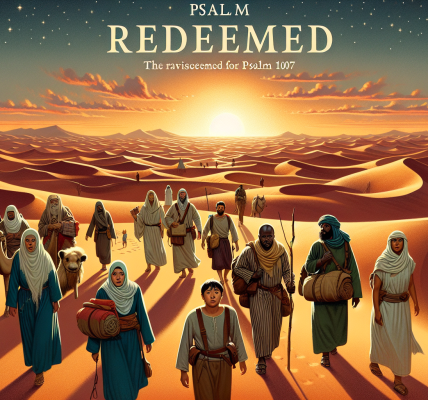铜尺是冰凉的,指节抵在上面久了,隐隐发麻。哈拿尼靠着半截斑驳的石墙,望着眼前这片杂乱无章的家园——耶路撒冷,名字依然尊贵,身形却像一个被扯烂又被胡乱缝补的麻袋。归回的人,像他一样,眼里燃着火,手上却满是无力。城墙依然断裂着,如同一个未愈的伤口,裸露在迦南地的风里。
那天下午,日头毒得很,铜色的光泼在碎石与荒草上。哈拿尼在琢磨一段墙基的走向,心里盘算着石料。恍惚间,似乎有人影在不远处走动。他起初没在意,归回的人日渐增多,生面孔寻常。但那人的举止有些特别,不像在丈量土地,倒像在……凝视某种看不见的轮廓。
哈拿尼眯起眼。是个少年人,衣着洁净得与这废墟格格不入,手里拿着一卷似乎也是铜制的准绳。他走得缓慢,专注,步子迈过残垣时轻盈得不沾尘土。哈拿尼的喉咙有些发紧,一种奇异的肃静感包裹过来,连风声都低了。
少年人走到哈拿尼近前,停了。他转过脸,面容清晰,眼神却像望穿了极远的年代。“你去告诉那少年人,”他开口,声音不高,却带着一种山涧回响般的质地,直透心底,“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,如同无城墙的乡村,因为其中的人民和牲畜甚多。”
哈拿尼怔住,四下并无其他“少年人”。这话,是对他说的?他成了传言的信使,而那传话的对象,竟就是眼前这位?他舌头发僵,一个字也吐不出。少年人——或者说,那使者——却已转身,继续他的“丈量”。他手中的准绳并未真正抛出,只是虚握着,但哈拿尼分明感到,一种远比石墙更稳固的界限,正随着那无形的步履被确立。
使者再次停下,这次是望着更广阔的天际,仿佛看见了哈拿尼看不见的旌旗与营垒。“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,并要作其中的荣耀。”这句话落下时,哈拿尼背脊掠过一阵颤栗。火城?不是砖石的屏障,而是烈焰的围墙?护佑与威严,竟以如此可畏又可靠的形式应许。他想起旷野中引领列祖的云柱火柱,那不曾熄灭的看顾。
接下来的话,让哈拿尼几乎站立不稳。使者的声音陡然拔高,带着一种席卷列国的宣告之力,指向北方,指向那曾经掳掠他们的巴比伦(他用了“北方之地”的隐语,但哈拿尼听懂了)。“嗨!嗨!你们要从北方逃回!”那呼声不是建议,是命令,是释放的号角。哈拿尼眼前仿佛出现了黑压压的人群,推倒精神的桎梏,挣脱富足的假象,从那些自以为安置妥贴的“香柏木高楼”中奔涌而出,向着锡安,归回。
“与巴比伦女子同居的锡安民哪,应当逃脱。”这句话像一根细针,扎进哈拿尼心里最混杂的角落。逃脱,不仅是从地理上的异乡,更是从那种与之“同居”的妥协、习惯、乃至隐秘的眷恋。真正的归回,是心灵彻底转向。
寂静重新降临。使者看向哈拿尼,最后的言语,柔和下来,却带着万军之重的根基:“万军之耶和华说,在显出荣耀之后,祂必差遣我去攻击那掳掠你们的列国……”祂?差遣“我”?哈拿尼脑中一片混沌,又似乎有一道闪电劈开迷雾。这使者是谁?他提及那最终的差遣者时,语气如此独特。
最后的话,是古老的应许在新时代的回响,直接对着这废墟,对着每一个耳朵发鸣的归回者:“耶和华必收回犹大作祂圣地的分,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。”收回,拣选。不是因为他们配得,而是因为祂的约永不废弃。全地的人,都当在祂面前肃静,因为祂已从祂的圣居所兴起,行动了。
幻象般的场景褪去。铜尺还在手中,冰凉。日头西斜,在断壁残垣上拉出长长的影子。但哈拿尼所见的,不再是绝望的废墟。他看见一座无墙的城,熙熙攘攘,生命与繁荣多到任何城墙都框不住。他看见一圈寂静燃烧的烈焰,温柔地舔舐天际,将一切敌意与恐惧隔绝在外。他看见四面八方,有衣衫褴褛却眼神明亮的同胞,正越过山岭,奔向这里。
他慢慢站起身,拍去衣上的尘土。手不再发麻,心里那份属算石料的焦躁,不知何时平息了。工程仍要继续,一砖一瓦。但驱动这双手的,不再仅是人的热忱,而是一个确据:这城,连同其中的人,早已被另一种不可见的准绳量度过,被一个烈焰的应许环绕,被一位从圣居所兴起的君王,牢牢地握在手中。
他望向西边最后一抹霞光,那里仿佛仍跳动着那“火城”的余温。该去找那些灰心的同伴们,喝点淡酒,吃块无花果饼,然后,把这些“看见”和“听见”,结结巴巴地,却真实地,告诉他们。夜风起来了,带着凉意,吹过耶路撒冷的废墟,哈拿尼却觉得,这是他归回后,第一次感到温暖的夜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