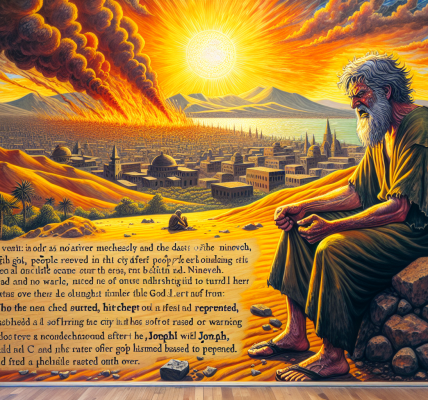海风带着咸涩的气息,卷过加利利沿岸的碎石滩。西门甩了甩手上的水渍,粗麻布的袖口已被浪花打湿大半。昨晚的收获寥寥,几尾小鱼在舱底徒劳地张合着嘴。安德烈蹲在船头补网,粗大的手指捏着骨针穿梭,动作里透着疲倦。
“听说那老师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境内。”安德烈头也不抬地说。
西门嗯了一声,望向北方。那片土地对他们这些南边湖上的渔夫而言,有些陌生,带着异邦的气息。希律王的领土,罗马的势力,还有那些古老异教的遗迹——潘神的洞窟,凯撒的庙宇。他不明白老师为何要往那里去。
但他们还是去了。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上走,空气渐渐变得清冽,松涛声取代了海浪的喧哗。路旁的岩缝里还积着前几日落的雨水。老师走在前面,背影在正午的日光下拉得很长,有时他会停下来,等着后面这群气喘吁吁的人。雅各和约翰在争论什么,声音压得很低,却依然能听出火气。西门没理会他们,他注意到老师的沉默比往日更深。
他们在一片缓坡上歇脚。下方山谷里,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城池轮廓隐约可见,更远处,雪白的庙宇柱廊在阳光下刺眼。那是另一个世界,是刀剑、赋税与皇帝雕像的世界。而他们这群人,穿着沾满尘土的草鞋,怀里揣着干硬的饼。
老师转过身,面向他们。风拂动他额前的发丝。
“人说我人子是谁?”他问。
问题来得平静,却像石子投入深潭。众人愣了一下,随即七嘴八舌地说起来。有人说,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;有人说,是以利亚,那乘旋风升天、传说必在弥赛亚之前归来的先知;也有人说,是耶利米,或是众先知里的一位。
西门的目光没有离开老师的脸。那些答案在空气中飘荡,却仿佛都没有触及那沉默的核心。他听着同伴们的议论,心里却涌起别样的东西。不是推理,不是猜测,更像是一种在黑夜拉网时突然感知鱼群方位的直觉——一种沉甸甸的确信,从记忆的深处浮起:约旦河边的洗礼,水珠从他发梢滴落;迦拿婚宴上无声流转的喜悦;还有那许许多多疲惫跋涉的黄昏,老师眼中那种既近又远、既温柔又威严的光。
他听见自己的声音,比想象中更粗粝,盖过了其他人的嘈杂:
“你是基督,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
话一出口,连他自己都静了片刻。坡上只有风声。所有眼睛都转向他,有惊愕,有茫然,也有若有所悟的闪烁。
老师的眼神落在他身上,那目光里有暖意,有重量,还有一种……近乎悲伤的赞许。老师向他走来,手掌按住他结实的肩膀。西门能闻到老师外衣上阳光与尘土的味道。
“西门巴约拿,你是有福的。”老师的声音不高,却字字清晰,仿佛刻入山岩,“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,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”
老师顿了顿,目光似乎越过他,望向更辽远之处。然后,他说出了那句让西门终身铭记的话:
“我还告诉你:你是彼得,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,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,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,在天上也要捆绑;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,在天上也要释放。”
彼得。磐石。这名字像一块真正的石头,沉甸甸地压进西门的生命里。他,一个冲动的渔夫,一个说话常不经过思量的人,磐石?他握了握自己粗糙的手掌,那里只有常年拉网磨出的硬茧。
后来,老师开始说起别的事,说人子必须上耶路撒冷去,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,并且被杀,第三日复活。这些话像冰冷的铁钉,猝然刺入刚刚被“天国钥匙”点燃的热望里。彼得猛地扯住老师的衣袖,动作急切得近乎失礼:
“主啊,万不可如此!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”
老师的眼神瞬间变了。刚才的温和荡然无存,那目光锋利得像刀,直刺过来。他转身对着彼得,声音里带着彼得从未听过的严厉:
“撒但,退我后边去吧!你是绊我脚的,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,只体贴人的意思。”
彼得的手像被烫到般缩回。撒但?绊脚石?方才的“磐石”与此刻的“绊脚石”,在短短片刻间,竟都是他。他踉跄后退一步,脸上火辣辣的,不只是因为当着众人的面受斥责,更是因为内心被洞穿的羞惭与惶惑。体贴人的意思……是的,他刚才只想到苦难与死亡的可怖,只想到跟随一位得胜荣耀的弥赛亚,却全然忘记了老师常说的“父的旨意”。
老师招呼众人继续前行,话语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,像是说给彼得听,也像是说给每一个心中藏着人意的门徒:
“若有人要跟从我,就当舍己,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,必丧掉生命;凡为我丧掉生命的,必得着生命。”
队伍沿着山路缓缓移动。彼得落在最后,脚步沉重。他回味着那两番截然不同的话,像咀嚼一枚橄榄,先有剧烈的苦涩,而后才有隐秘的回甘。磐石与绊脚石,钥匙与十字架,得着与丧掉……这些矛盾在他心中冲撞,尚未理清,却奇异地共存着。
暮色开始染红西边的山脊。老师的身影在前方,正走向那片愈发浓重的阴影,也走向耶路撒冷的方向。彼得抬起头,深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。肩头仿佛既压着一把看不见的钥匙,又压着一副未成形的木架。他迈开步子,跟了上去。脚下的碎石,在黄昏里,坚硬如铁,也沉默如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