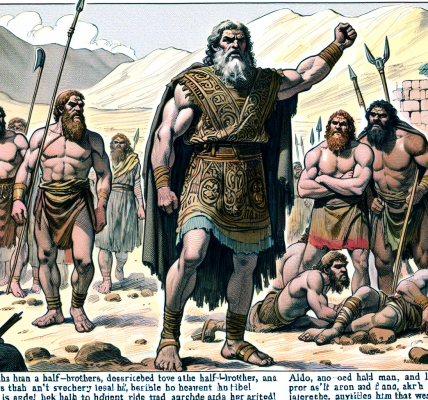烛火在石墙上投下抖动的影子。这不是圣殿里的金灯台,只是我家中一盏普通的陶土灯。夜很深了,耶路撒冷的喧嚣早已沉入地底般的寂静。我,以利亚布,一个曾站在王面前进言的臣子,此刻却连抬手拂去额上冷汗的力气都稀薄如雾气。
一切都始于一次微不足道的骄傲。王赞赏了我为扩建水道提出的谋略,酒宴上,贵胄们的恭维像蜂蜜涂满耳朵。我记得自己站在宫殿的高台上,俯瞰层层叠叠的屋宇,心里有个声音在低语:“以利亚布,你的根基如锡安山,永不动摇。” 我甚至忘了睡前向耶和华低声祷告,只觉得身下的锦褥格外柔软,明日的光辉触手可及。
转折来得毫无征兆。仿佛一夜之间,力气从我骨缝中流走,像沙漏里的细沙。起初是清晨起身时的眩晕,接着是肋间隐隐的、持续的低热,像一块在灰烬里埋着的炭。最优秀的医师按过我的脉,翻看我的眼睑,最终只是摇头,留下一些气味苦涩的膏药。王遣人送来慰问,但宫门前的台阶,我已数月未能踏足。
疾病是个耐心的盗贼,一点点偷走我的一切。皮肤紧贴骨骼,曾经能拉开硬弓的手臂,如今连盛满水的铜杯都端不稳。夜晚最难熬。高热如浪潮拍打,我在汗湿的床榻上辗转,听见的只有自己粗重的喘息和窗外无边的死寂。朋友们起初常来,后来渐渐稀少,最后只剩下老仆俄备得沉默地进出,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我熟悉的悲哀——那是人们在等待结局时的神情。
有一夜,我觉得自己到了边缘。黑暗从房间角落弥漫过来,带着墓穴的寒气。我忽然想起年少时在伯利恒野地里看过的景象:一只失群的羊羔跌入岩缝,它的哀鸣细弱,却持续不断,直到牧人俯身将它抱起。那一刻,没有智慧的话语,没有臣子的体面,我像那个最原始的受造之物,从喉咙深处挤出破碎的声音:
“耶和华啊,你曾将我提拔,不叫仇敌向我夸耀。如今你要将我扔下深渊么?求你怜恤!救我!”
没有闪电,没有声音。只是在我哭喊之后,疲倦如厚重的羊毛毯将我裹住,我竟沉沉睡去,连梦也没有。
改变是从一次睡眠开始的。不再是昏沉,而是真正沉睡,像婴儿蜷在母亲怀里。次日清晨,我睁开眼,看见一缕天光从高窗斜射进来,灰尘在光柱中缓缓旋舞。一种久违的、对清水的渴望浮起。我轻声唤俄备得。他端着水罐进来,看见我试图自己撑坐起来,陶罐几乎脱手。
力量回来得缓慢,如同春天的溪流融化坚冰。我能坐起了,能倚着窗口看橄榄山岗上的绿意了。有一天,俄备得搀扶着我,迈过那道高高的门槛,站在自家的院子里。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泻在我身上,温暖得让我战栗。我仰起脸,闭着眼,感觉那光穿透眼皮,是一片血红而活着的颜色。我忽然泪流满面。
“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,”我喃喃自语,声音沙哑,“将我的麻衣脱去,给我披上喜乐。”
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以利亚布了。宫中的事务依然重要,但当我再次走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,石头路的凹凸,市集上香料的气味,妇人头顶水罐的平稳姿态,甚至墙角一丛挣扎着开出的野花,都让我感到一种崭新、尖锐的鲜活。我更深地明白了大卫王诗句里的含义:“一宿虽然有哭泣,早晨便必欢呼。” 那“早晨”并非仅是黑夜的终结,而是一种本质的更换,是绝望的粘土被重塑为感谢的器皿。
如今,我常在暮色中登上我家平坦的屋顶。远处圣殿的轮廓映着夕阳,炊烟从千家万户缓缓升起。我抚摸着自己曾经嶙峋、如今渐渐覆上柔软的手腕,心里没有狂喜,只有一片深湛的宁静。我知道生命如雾气,疾病如暗处的埋伏,我的“根基”从未是那座宫殿,也不是我自己的才智。
我将我的故事告诉愿意听的人,不是作为奇迹,而是作为一个见证: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,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黑夜的哭泣或许漫长,但总有应许的晨光,会温柔地叩响每一扇看似永远关闭的窗扉。
灯火渐暗。我吹熄了它,在黑暗里坐着。寂静中,我仿佛又听见了那单纯如羊羔呼喊的祷告,而这一次,我知道回应早已在路上了,如同黎明必定追赶黑夜的脚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