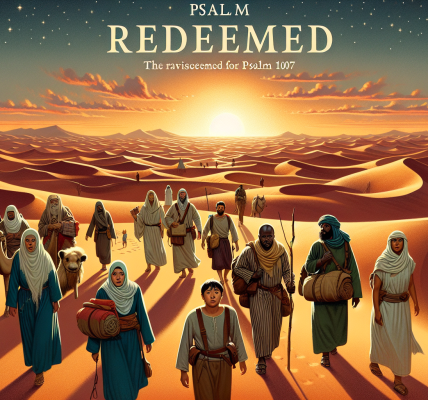旷野的风,已经吹了许久。它刮过乔布破烂的衣裳,卷起沙粒,打在那些尚未愈合的毒疮上,带来一阵细微却尖锐的刺痛。但乔布已经几乎感觉不到了。他坐在炉灰中,身体里先前那股沸腾的、混合着冤屈与质疑的灼热,已在连日来的争辩和那从旋风而来的声音中,渐渐冷却,变成一种沉重的、遍布四肢百骸的疲惫。
然而,那从旋风里发出的声音并未停歇。它不像雷,也不像他任何一位朋友的劝诫。它低沉,浑厚,充满了整个天地,却又仿佛直接响在他的骨髓里。
“…强辩的,岂可与全能者争论么?指教神的,可以回答这一切罢。”
乔布的嘴唇动了动,干裂的皮撕开,渗出一丝腥甜。他想低头,脖颈却僵硬如石。他想抬手遮住眼睛,避开那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注视,手臂却重得抬不起分毫。风更烈了,不再是燥热的风,而是带着深谷寒意的、仿佛来自太初之时的气息。他听见自己的心跳,在那一句句问话的间隙里,像绝望的鼓点。
于是,他只能用尽残余的力气,将脸埋向沾满尘灰的掌心,声音嘶哑,几乎被风吹散:
“我是卑贱的。我用什么回答你呢?只好用手捂口。”
他停顿,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胸口的窒闷。“我说了一次,再不回答。说了两次,就不再说。”
寂静。风也仿佛屏息。旷野的巨石、枯干的荆棘、远处模糊的山影,都在等待。乔布等待着最终的判决,或是更猛烈的风暴。他预备承受一切。
但那声音再次响起,却并未宣判。它转向了另一个方向,仿佛一位巨匠,要向他展示另一件作品。
“你且观看河马。”
这称呼让乔布微微一怔。不是他所熟悉的任何牲畜的名字。那声音继续着,不疾不徐,描绘着一个他既陌生又仿佛在梦中见过的形体:
“我造你也造它。它吃草与牛一样。它的力气在腰间,能力在肚腹的筋上。它摇动尾巴如香柏树,它大腿的筋互相联络。它的骨头好像铜管,它的肢体仿佛铁棍。”
意象开始在他脑海中拼凑。不是温顺的牛羊,不是迅捷的猎豹。是一种笨重、坚实、充满了原始蛮力的存在。他仿佛看见它卧在芦苇丛与沼泽的隐秘之处,巨大的身躯半浸在幽暗的水里,垂柳的枝条拂过它岩石般的背脊。它的尾巴摆动时,不是驱赶蚊蝇,而是像一棵移动的、有力的树木,搅动一池静水。
“它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。”
这句话落下,带着不容置疑的重量。为首?乔布混乱地想。不是凌空翱翔的鹰,不是威猛无俦的狮子,而是这卧于泥泞水泽、以草为食的巨兽?
“有谁能到它面前,拿住它,用笼头穿它的鼻子呢?”
一幅画面陡然清晰:有人试图靠近,绳索与钩叉在日光下闪烁。但那巨兽只是略一摆首,或许仅仅是一个起身的动作,那些精巧的器械、那些人的勇气与计谋,便像脆弱的芦苇般折断、崩散。它不属于人的牧场,不屈服于人的围栏。它安然居于自己那片丰茂却也危机四伏的领地,本身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,一个活生生的、关于“界限”的启示。
乔布掌心的皮肤,感受着自己微弱的呼吸。炉灰的粗糙,此刻异常真实。他忽然明白了。这不仅仅是在描述一头奇兽。
他先前所有的诘问,关于善恶的分布,关于自身遭遇的公义,都建立在一个隐约的假定上:他,乔布,能够理解神治理世界的蓝图,能够评判那蓝图中的每一笔线条。他用自己的尺度——尽管那是正直的尺度——去丈量无限的深渊。
而河马,这神所造的、在它所辖领域里“为首”的巨物,安然卧于其位,对人类的计量一无所知,也毫不在乎。它不证明什么,不解释什么,它只是“存在”着,以其庞大而沉默的存在,宣告着创造主那超越理解的设计与权能。人不能驯服它,甚至不能真正接近它,正如人不能靠智慧窥透命运的经纬。
风仍在吹,但乔布身体里那沉重的疲惫,开始起了一丝变化。并非消散,而是沉淀,混入了一种新的、近乎敬畏的寒意。他的苦难没有被解答,他的疑问依然如荆棘刺在心头。但那些问题,似乎被放置到了一个更宏大、更幽深的背景之中——一个容纳河马与深渊、维系星宿与雏鸟、其道路非人智可测的背景。
他仍旧坐在炉灰里,疮口依然疼痛。但当他再次慢慢抬起头,望向旷野辽远而变幻的天空时,眼神里某种固执的火焰熄灭了,取而代之的,是映照着深渊的、晦暗而不安的平静。
那声音还在继续,转向了海洋的巨物。但乔布知道,关于河马的这一段,已经足够了。它像一个沉重的锚,将他所有翻腾的思绪,牢牢定在了敬畏的深渊之畔。答案仍未显明,但质问的嘴唇,已被这沉默的巨兽,温柔而有力地合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