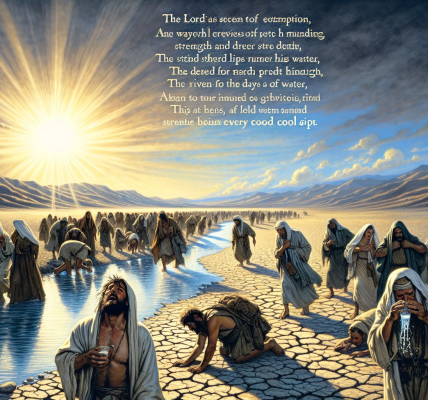晨曦初露,耶路撒冷城外的橄榄山还浸在青灰色的薄雾里。石板路上传来缓慢的脚步声,是亚里达,一个从大数来的布匹商人。他肩上搭着的羊毛披风被露水打湿了边缘,手里攥着一卷磨损的莎草纸。纸上是他在罗马经商的表兄托人带来的信,字迹潦草,却反复提到一个陌生的名字:保罗。
亚里达这次来耶路撒冷,本是为了处理一批染坏的紫色布料。生意谈得并不顺利,心里的烦闷像卡在喉头的橄榄核。信是在客栈昏暗的油灯下读的,表兄的话跳跃而热烈,讲一个难以置信的道理:“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,是受洗归入他的死……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,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”亚里达不懂。死亡与新生,这和他染缸里失败的颜料、集市上锱铢必较的争吵有什么关系?
他不知不觉走到一处废弃的石凿水池边,池底积着浑浊的雨水和枯叶。靠着池壁坐下,亚里达望着水面自己的倒影——一张被旅途和算计刻上细纹的脸。他想起了自己的洗礼。那是许多年前在约旦河,河水冰凉刺骨,浸没时耳边是嗡嗡的水声和施洗者模糊的吟诵。出来时浑身湿透,打着寒颤,心里确有一阵短暂的清澈,仿佛旧日的污秽被冲刷而去。可后来呢?贪婪仍旧在讨价还价时掐紧他的喉咙,恼怒仍在伙计算错账目时烧红他的脸颊。那次的浸没,似乎只是另一个需要完成的仪式,如同他行过无数次的洁净礼。
一只灰雀扑棱着落在池边,啄食着石缝里的草籽。亚里达看着它,忽然觉得自己的信仰也像这池水——静止的,与生活隔着一层厚厚的、无法穿透的边界。表兄信里却说,洗礼不是水池,是坟墓。不是洗净,是埋葬。
他闭上眼,试图想象那个场景:不是身体浸入水中,而是整个旧我,连同它的恐惧、它的贪婪、它对得失的执念,被放入一个凿好的石墓,然后有沉重的石头滚过来,封住洞口。那该是怎样的黑暗与终结。他不禁打了个寒噤。
不远处的农舍传来炊烟的气味,混合着烤饼的焦香。生活仍在继续,日复一日。如果旧我已被埋葬,那么此刻坐在这里的又是谁?信里的句子浮现:“这样,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;向神在基督耶稣里,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”看自己是死的——亚里达咀嚼着这个词。不是感觉,不是情绪,甚至不是立即的、焕然一新的改变。是一种认定,一种基于事实的判断,像商人确认一笔债务已经勾销,哪怕债主的面孔还在记忆里徘徊。
他想起自己作坊里一个老染工。老人双手浸染过无数颜色,指甲缝里积着洗不掉的靛蓝与绛红。有一次他告诉亚里达:“最难染的,其实是白布。你必须相信它本来是白的,才能染出最纯粹的颜色。如果你总当它是脏的,染什么都会发污。”亚里达当时只当是老人的玄虚之谈,此刻却像一道微光透进来。或许“看自己是死的”,就是承认那旧的、污秽的底布已经不存在了。现在展开在神手中的,是一匹新的、洁白的细麻布。
风穿过橄榄树林,发出沙沙的声响,像无数细小的耳语。亚里达摊开手掌,晨光落在掌心的茧子和一道陈年的伤疤上。这双手曾为多得几个铜板在秤砣上做手脚,也曾因怜悯悄悄多量一肘布给丧夫的妇人。罪与义,死亡与生命,竟如此错综地交织在这血肉之躯里。信上说:“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,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”作王——这个词让亚里达心头一震。罪不是偶犯的过错,它是一个篡位的王,盘踞在他生命的宫殿里发号施令。而洗礼所宣告的埋葬,正是要废黜这个王。
他缓缓站起身,膝盖因为久坐而有些僵硬。雾气正在散去,阳光开始温暖他的后背。回城的路上,他经过一个正在翻耕的田地。农人吆喝着牛,锋利的犁铧切开板结的土块,将枯槁的残茬深深埋入地下,翻出底下湿润的、深褐色的新土。亚里达停下脚步,看了很久。埋葬,不是为了停留在黑暗里,乃是为了那被翻搅出来的、能够孕育的新土。
他并非忽然间感到狂喜或轻松。那旧我的习性,如同田里顽固的根茎,或许还会在新土里冒出芽来。但不同之处在于,他如今知道,那已不是真正的“他”了。真正的他,是那个与基督一同被埋葬,又一同活过来的生命。这生命不在他感觉的起伏里,而在一个更深的、由神宣告的事实之中。就像他手中这封皱巴巴的信,无论他读时是明白还是困惑,信上的字迹已然存在,不容更改。
亚里达将信仔细折好,放入怀中贴着胸口的地方。他抬头望向耶路撒冷的城墙,在越来越明亮的日光下,那些巨大的石块呈现出一种温暖的蜂蜜色。城里,他的染缸还在,算盘还在,纷争与诱惑也必然还在。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他迈步向城门走去,脚步比来时似乎轻省了些,却又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郑重,仿佛一个被废黜的君王正学习像自由的平民那样走路。路边的无花果树下,几个孩童在嬉戏,笑声清脆。亚里达看着他们,嘴角不自觉地微微扬起。新生或许不是一声巨响,而是这样一步步的、学着在已然赐下的自由里,重新开始行走。而这条路,正从这座埋葬了旧我的坟墓——或者说,从这池他曾以为只是仪式的水——开始,延伸向日光之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