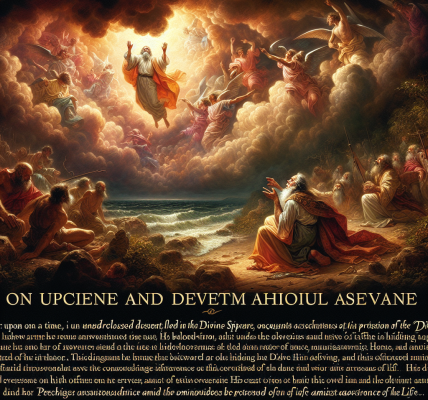窑匠的手,是粗糙的,指节突出,覆着一层洗不净的暗红黏土。他坐在耶路撒冷城外一间半塌的棚子里,脚边的转盘空着,像一只等待的眼眶。我看着他,看着那双此刻静止的手,忽然想起以赛亚的话——“耶和华啊,你是我们的父;我们是泥,你是窑匠。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”
这话,如今听来像一声呛在喉头的叹息。
耶路撒冷的城墙是修补过的,像一件打满补丁的旧衣,粗粝的石头缝里,新灰浆的颜色浅得刺眼。圣殿立在那里,当然,比被掳之前小了许多,也寒酸了许多。夕阳给它镀上一层脆弱的金箔,仿佛一碰就会碎掉。我们回来了,从巴比伦的河边回来了,可我们带回的,不只是犹大家的余民,还有一种更深的、骨子里的荒芜。我们盖起了房屋,我们筑起了祭坛,我们按着节期献祭,一切都对,一切又都不对。仿佛灵魂与仪式之间,隔着一层厚厚的、无声的雾。
我坐在一块断碑上,灰尘钻进麻衣的纤维。远处的山谷升起晚炊的烟,笔直地,脆弱地,升到半空就被风吹散。这景象让我想起先知的话:“……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。那时你降临,山岭在你面前震动。”
山岭震动?如今什么也不震动。连祷告都似乎撞到了铜铸的天顶,沉闷地跌回尘土。我们呼喊,却像在空旷的峡谷里自言自语,只有自己的回声应答。我们的义,在长久沉默的上帝面前,都像污秽的衣服,被自己经年的罪浸透,发出陈腐的气味。风起来了,卷起街角的沙土和枯叶,扑打在脸上,细微的疼。这风是否也曾刮过以赛亚的年代?那时,上帝似乎更近,他的愤怒如烈火,他的拯救也如磐石般确凿。而今,我们活在一种漫长的、温吞的等待里,一种不上不下的煎熬中。我们求他“撕裂诸天而降”,让群山再次在他面前熔化,像火烧炼蜡那样。我们宁愿要那可畏的临在,也不要这无边的、磨人的寂静。
棚子里,窑匠终于动了。他舀起一勺水,泼在那一堆黯红的黏土上。那土,是从汲沦溪谷旁挖来的,里面混着细碎的砂石和往昔的陶片。他开始揉,用全身的力气压、按、折叠。那不是一个温柔的过程。黏土在他掌下呻吟、变形,内部的空隙被狠狠挤压出去,砂砾硌着他的皮肤,也可能硌着土本身。这不是创造,这是征服,是重塑。我看着,忽然感到肋间一阵钝痛。我们,不就是这团待揉的泥么?里面掺着巴比伦的砂砾,掺着在异邦学来的偶像碎屑,掺着怯懦、抱怨,和一种连自己都厌弃的麻木。
窑匠把泥重重摔在转盘中央。脚一蹬,轮子转起来,起初有些滞涩,吱呀作响,随后变得平稳,发出低沉的嗡鸣。他的双手拢住那团旋转的混沌,微微向上提引,一个模糊的形体便从中生长出来。那是极专注的时刻,他的呼吸似乎都与转轮的节奏合一。泥柱在他指尖颤动,湿润,顺从,仿佛有了生命。
可忽然,毫无征兆地,那正在成形的器皿壁上,出现了一道细微的、扭曲的裂痕。或许是一粒未曾揉匀的硬砂,或许是泥料本身的疲弱。窑匠的动作停了。他凝视着那道裂痕,眼神里没有惊讶,只有一种深沉的、几乎是悲伤的了然。他沾水的拇指试图去抹平它,但裂痕反而扩大了,在旋转中蔓延,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。整个形体开始失控地摇晃, wobbling,失去了中心。
他没有犹豫。双手猛地一合,将那初具雏形的瓶罐,重新压垮成一团混沌的泥。哗啦一声,伴随着更多水的泼溅,一切归零。轮子还在转,但那上面只剩下了一摊不成形的、疲软的泥浆,顺着离心力微微摊开,像一声失败的叹息。
我猛地闭上了眼。心里那声呼喊终于冲破了喉头的阻塞:“耶和华啊,求你不要大发震怒,也不要永远记念罪孽;求你垂顾我们,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。”
我们是他手下的泥。我们曾是尊贵的器皿,却自己裂开了缝隙。我们在这片他应许之地,却活得像无家可归的游魂。圣城荒凉,锡安变为旷野,那荣耀的殿,我们的心,何尝不是?我们等候他,像在干旱无水之地等候云霓,但天,始终是铜色的,坚硬地沉默着。
风停了。黄昏的最后一丝光,沉入西山。棚子里,窑匠正在清理转盘,把那团失败的泥刮下来,扔回角落的瓦盆。也许明天,他会再揉,再试。也许那泥里终究能出一个合用的器皿。
我站起身,麻衣上沾满了碑石的凉意。夜气升腾,笼罩着这修补的城,这等待的民。群山在渐浓的暮色里只剩下黝黑的轮廓,稳稳地,沉默地,伏在大地之上。
我知道,那震动山岭的,使火着起的力量,并未消失。它只是隐藏在沉默之后,在窑匠下一次揉泥的手劲里,在绝望的祷告最深处,那不肯熄灭的余烬中。我们等待,不是等待一个答案,而是等待那双手,再次,不容抗拒地,握住我们这团充满裂痕的泥土。
毕竟,我们是泥。他是窑匠。
除此之外,我们一无所有。除此之外,也是一切盼望所在。
夜色,完全降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