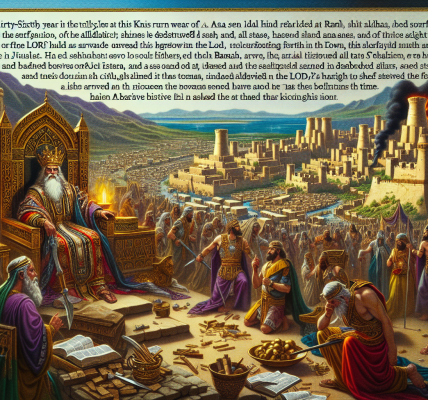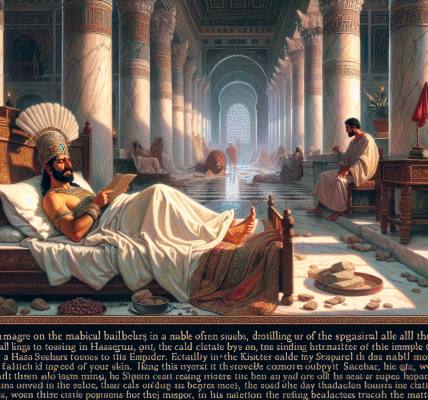那封信送到的时候,海港城市哥林多正弥漫着晨雾与鱼市的气息。羊皮卷轴搁在阿迦彼家的木桌上,边角被海风浸得微潮。送信的以弗所水手只说,是保罗托的,便匆匆赶回码头去了。那时,亚波罗刚离开不久,矶法的门徒还在城北的会堂里低声议论着,而基督的名,像一枚投入这锅沸腾汤水的盐,滋味正扩散,也正被各样的滋味拉扯。
我,一个在染料作坊记账的,名叫马可的,便是那日坐在阿迦彼家昏暗里屋的几人之一。油灯的光晕摇晃,照着读信人格外严肃的脸。他是从罗马来的路求,声音沙哑,仿佛喉咙里也积着哥林多的灰尘。
“奉神旨意,蒙召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……”
声音响起时,外面街市传来小贩尖利的叫卖,混合着陶器碰撞的脆响。路求皱了皱眉,继续念下去。信的开头是温厚的,问安,感恩,提醒我们蒙了何等的恩惠,在知识、口才上一样都不缺。屋角的老织工约拿单点了点头,他粗糙的手指捻着衣角,那是他听了亚波罗精彩的讲道后,坚持要换上的细麻衣。空气里有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、微妙的满足。是啊,我们这混杂的教会——有犹太的帐幕匠,希腊的哲人学徒,罗马释放的奴隶,还有像我这样无足轻重的小人物——竟被那位远在以弗所的使徒如此称许。
然而,路求的声调沉了下去,像船锚探入深水。
“弟兄们,我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,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。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……”
“分党”一词落下,屋里倏地静了。只有隔壁染缸里,紫贝浸液冒泡的咕嘟声隐约传来。我们互相看了看,又迅速移开目光。怎能不分呢?矶法的追随者说,要守古老的律法和割礼,那是根基;亚波罗的仰慕者陶醉于他雄辩的言辞和深邃的寓意解经,那智慧如亚历山大港的灯塔,照亮人心;至于那些直接奉保罗名的人,则昂首宣称自己得了福音的真自由,不受旧约规条的捆绑。而我,有些夜里,我躺在窄床上,听着老鼠在梁上奔跑,心里一片茫然。我只是被“基督耶稣”这个名字里某种难以言喻的、牺牲的爱所打动,可这爱,在那些日益高亢的争辩里,似乎变得模糊了。
路求的声音继续着,保罗的话像一把钝刀,开始剥开我们光鲜的表皮。“基督是分开的么?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么?” 问得如此直白,令人面皮发烫。我们争来争去,仿佛基督成了一块可以分割的地产,或是市场上可以标价归属的货物。
然后,信进入了最令人费解,也最让当时的我们——尤其是像我这样,在希腊修辞学堂外偷听过几句的人——感到刺耳的部分。保罗竟说,神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;又说,犹太人是要神迹,希腊人是求智慧,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这基督,在犹太人眼里是绊脚石,在外邦人看来是愚拙。
“愚拙。” 路求念出这个词时,停顿了一下。我瞥见对面那位哲人学徒尼科拉俄斯,嘴角不易察觉地撇了撇。他曾向我展示过一卷柏拉图的对话录,羊皮光滑,墨迹工整。智慧、逻辑、宇宙的理性(Logos),那才是通往真理的道路。一个被罗马士兵像最卑贱的奴隶般处死的神?这不仅是愚拙,简直是亵渎。
信还在往下念,但我的心绪已经飘开。我想起上个安息日后的争吵,在集市柱廊的阴影下。矶法的一位支持者,和亚波罗的一位崇拜者,为了“ baptism (洗礼)的真正形式”争得面红耳赤,引经据典,直到一位路过的罗马百夫长投来嫌恶的一瞥,他们才噤声,但眼里仍烧着不服的火。那时,我心里涌起的不是对某方道理的赞同,而是一种深深的疲惫,还有一种……羞耻。我们声称拥有的那位主,那位谦卑服事、为仇敌祷告、最终无声地走向各各他的主,在我们的喧嚣中,似乎悄然退到了最远的背景里。
保罗写道:“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,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”
油灯的灯花爆了一下。路求抬起眼,目光缓缓扫过我们每一个人。老约拿单捻着衣角的手停住了。尼科拉俄斯紧锁的眉头没有松开,但眼中的傲气似乎被这截然不同的“智慧”定义,撞开了一丝裂隙。而我,那个在染料和账目间蝇营狗苟的马可,心里那一片茫然的海,仿佛被投进了一块巨石。不是逻辑的巨石,不是神迹的巨石,而是一块粗糙的、带着血污的、十字架的木头。
不是靠压倒对方的才智取胜,也不是靠炫目的灵异现象征服,而是用一种最彻底的“软弱”——牺牲的爱,自愿的虚己,来颠覆这世间一切关于力量与智慧的尺度。这道理,对世界的眼光而言,何其愚拙!可就在这愚拙的宣告中,我那颗被各种派别口号弄得麻木的心,却感到一种奇异的、尖锐的苏醒。我们所有的“属灵归属感”、知识上的优越、口才上的比拼,在这“愚拙”的十字架面前,是否正如保罗所言,成了“废掉”那些聪明人、有能人、有贵族血统之人的工具?好叫任何人——染工、奴隶、哲人、税吏——都不能在神面前凭自己夸口。
信的最后部分,是关于“蒙召”的。我们中间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,有能力的不多,有尊贵出生的也不多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、软弱的、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……我环顾这间陋室,看着每一张被生活刻下痕迹的、平凡的脸。是啊,我们正是这样的人。这份拣选,不是为了让我们组成新的、更“属灵”的精英圈子,去轻视别的圈子,恰恰是为了“使一切有血气的,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”
路求读完了。卷轴轻轻卷起。很长一段时间,没有人说话。晨雾早已散尽,正午的阳光从高窗的缝隙刺入,照亮空气中浮动的无数微尘。外面哥林多的喧嚣依旧:辩论、交易、野心与享乐的海浪永不止息。
但在这寂静的屋里,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那争吵的欲望,那非要归属于某个“更正确”群体的焦躁,像潮水般退去,露出底部的礁石——那礁石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,不是任何人的产业,而是我们所有人共同仰望的、唯一的根基。
老约拿单慢慢站起身,走到屋角的水罐旁,倒了一杯水。他没有递给任何一位“派别”的领头人,而是递给了刚刚进屋、一直怯生生躲在门边的年轻奴隶女孩,她手里还捧着从市场买回来的蔬菜。他什么也没说。女孩惊讶地接过,眼里有光闪动。
尼科拉俄斯深深吸了口气,又缓缓吐出。他走到我身边,拍了拍我的肩膀,手指上还沾着学堂里的墨迹。“马可,”他说,声音有些干涩,“你作坊里……还有多余的、染坏了的次等布料么?我……想或许有人需要。”
我点点头,知道他不是在问布料。
我们陆续走出阿迦彼的家。哥林多的阳光灼热而真实,照耀着这座充满“智慧”与“能力”的城市。十字架的道理,依然是愚拙的,是绊脚石。但就在这愚拙之中,我们这群愚拙的、软弱的、蒙了呼召的人,仿佛第一次,跌跌撞撞地,开始学习不再建造属于矶法、亚波罗、保罗——或任何伟人——的宗派,而是学习去建造那唯一根基上的、虽然仍有裂痕却渐渐合一的房子。而这一切,都源于那封被海风浸湿的信,和信中那颠覆世界的、愚拙的智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