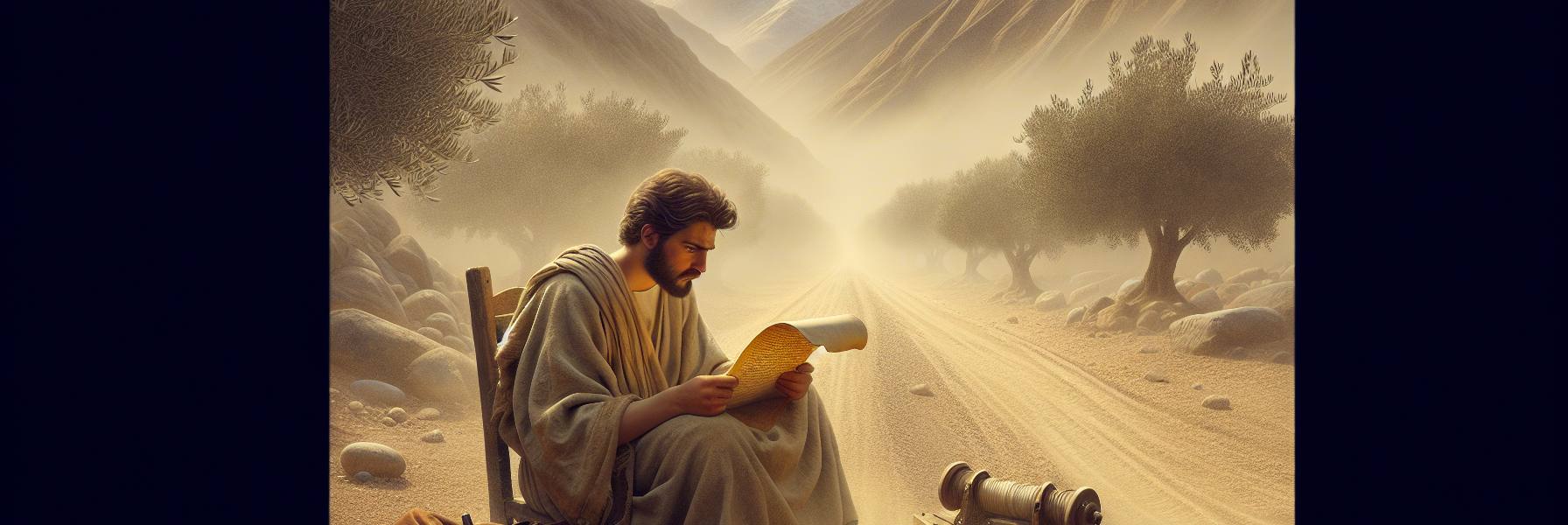黄昏的光斜斜地切进院子,把地上铺着的不规则石板照得一半暖黄,一半青灰。空气里有尘土、干草,还有一丝从西边飘来的、隐约的海盐气味。我蹲在廊柱的阴影里,打磨一只铜盆,手上的粗麻布来回蹭着,发出单调的“沙沙”声。手腕上的旧伤,在某个角度弯曲时,还会传来一阵熟悉的钝痛。我是个家生奴,生在这里,长在这里。这院子,这廊柱,还有主人家那些在午后安静时分隐约传来的说笑声,就是我全部世界的边界。
我记得老底嘉,我的母亲。她是服侍女主人的。在我很小时,她就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咳着血去了。她留给我的,除了一副与她一样瘦削的骨架,就是一句反复念叨的话:“要顺服,孩子,我们生来就是服侍的。”这话像一道烙印,滚进我的耳朵里,烫在我的脊梁上。我的生活由无数的“不可”编织而成:不可与主人同桌,不可在主人面前抬头太久,不可有属于自己的东西,甚至,不可有太多属于自己的念头。律例,规矩,时辰,活计……它们像一副看不见却沉重无比的枷锁,每日清晨我一睁眼,就准确地套在我的脖颈上。我惧怕犯错,因为犯错意味着责打,更意味着一种更深重的、仿佛被整个世界厌弃的孤立。我有时望着高远的天空飞过的鸟,会生出一种近乎窒息的渴望,但随即,那渴望就会被更深的恐惧压下——那是不属于我的位置,我僭越了。
主人是个罗马人,严肃,但不算暴戾。这个家真正的光,是他的独生子,名叫该犹。该犹与我年纪相仿,却活在截然不同的宇宙里。他不必劳作,穿着细麻衣裳,跟着请来的先生学习文法、修辞和哲学。他可以在庭院里自由奔跑、大笑,他的声音清脆得像银铃。最让我无法理解的,是他看着主人——他父亲——的眼神。那不是畏惧的躲闪,而是一种亲昵的、带着信任的坦然。他会扑进父亲怀里,分享他的见闻,甚至辩论。而主人,那位让我不敢直视的罗马人,会用手揉乱该犹的头发,脸上露出我从未见过的、柔和的笑容。
那笑容刺痛了我。不是出于嫉妒,而是一种更茫然的钝痛。我不明白,为什么同在一个屋檐下,呼吸同样的空气,他是儿子,而我只是产业的附属,一个“它”。我的存在,是为了让他的生活更加便利、安稳。这就是我与生俱来的“律法”,我无法逃脱的“夏甲”的命运。夏甲,另一个女奴的名字,我是后来听来的故事。她是被迫的,生了儿子,但那儿子并不能真正承受产业,最终要被赶出去。自由妇人所生的,才是真正的后嗣。这个故事像一片阴云,时常笼罩着我。我想,我就是那使女的儿子,我的名分是暂时的,我的位置是脆弱的,随时可能被那真正的、自由的儿子取代,然后被放逐到更深的荒芜中去。
转变发生得毫无征兆。那是一个异常闷热的午后,雷雨将至,空气黏稠得能拧出水。我因为打翻了一罐新调的颜料(是为该犹学习绘画准备的),正跪在院中受罚。鞭子没有落下来,主人和该犹似乎刚结束一场谈话,从内室走出来。主人看到了我,他眉头皱了一下,并非愤怒,而是一种……复杂的审视。他挥挥手,让拿着鞭子的管家退下。然后,他走了过来,阴影笼罩住我。
“抬起头。”他说,声音不高。
我艰难地抬起脖子,目光仍垂视着他华服的下摆。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他问。这问题让我茫然,他当然知道我的名字。
“以拉都,主人。”我声音干涩。
他沉默了片刻,雷声在天边滚动。然后,他说了一句让我浑身血液几乎冻结的话:“从今天起,你不是奴隶了。”
我猛地抬起头,第一次真正看向他的眼睛。那里没有戏谑,没有试探,只有一种平静的决断。
“我,路求,今日立你为我的儿子,与我亲子该犹同得产业。”
世界在那一瞬间失去了声音。管家倒吸冷气的声音,远处隐约的雷鸣,我自己的心跳,全都消失了。我只看见他的嘴在动,那些字句一个个砸进我的灵魂里,却重得我无法理解其含义。儿子?产业?和我?一个家生的奴仆?
该犹站在他父亲身边,脸上没有惊讶,只有一种纯净的、近乎喜悦的光芒。他对我笑了起来,那笑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少爷对仆役的宽容,而是……而是兄弟间的会心一笑。
仪式简单得近乎潦草,却又庄重得让我灵魂战栗。不是在会堂,没有祭司,就在这飘着尘土和颜料气味的庭院里。主人——现在,我能在心里尝试那个陌生的词汇了:父亲——他取来一枚带有家族印鉴的铁戒指,套在我粗糙肮脏的手指上。戒指很沉,冰凉的金属渐渐被我的体温焐热。他又拿来一件该犹的旧外袍,披在我满是汗渍和尘土的短衣上。袍子带着阳光和皂角的干净气味,将我整个包裹住。最后,他按着我和该犹的肩膀,把我们带到宅邸的正厅,那张我每日擦拭却从未靠近的长桌前。
“吃吧。”他说。
桌上摆着面包、橄榄和鱼干。不是残羹冷炙,是份例内的食物。我坐在坚硬的木凳上,手脚都不知该往哪里放。该犹掰下一块面包,很自然地递给我。我接过,放进嘴里,却尝不出任何味道。泪水毫无预兆地冲进眼眶,不是悲伤,不是喜悦,而是一种庞大的、将我彻底淹没的震颤。那副无形的、我生来就背负着的重轭,在那一刻,“咔嚓”一声,从我精神深处断裂、脱落了。
我不再是奴仆。我是儿子。
那天晚上,我躺在分配给我的、虽小却属于我的房间里,久久无法入睡。手指摩挲着那枚冰凉的戒指。我忽然想起了母亲,想起她枯瘦的面容和那句“要顺服”。她顺从了一生的“律法”,那奴役的体制,并没有给她带来自由,只带来了早逝的凄凉。而我,这个从未奢望过挣脱的人,却因着家主白白的、不可测度的恩典,被赋予了儿子的名分。这不是因为我打磨的铜盆更亮,也不是因为我犯的错更少。这完全出于他的心意。
这就像那应许之子,不是从律法与行为而生,乃是从信与恩典而来。夏甲代表西奈山约,生产为奴的;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,她是我们的母。我以前活在“夏甲”的影儿下,活在咒诅和惧怕里;如今,我被接入“撒拉”的应许中,成了自主妇人膝下的孩子。
身份变了,眼中的万物也都改了颜色。清晨的阳光不再意味着新一轮劳役的开始,而是恩典的新的凭据。主人的命令——现在是我父亲的吩咐——不再是一道道冰冷的、必须遵守否则就会受罚的禁令,而是一个孩子乐意去聆听、去顺服的智慧之言,因为我深知这言语背后的爱与保全。我甚至开始学习文字,和该犹一起。那些弯曲的字母不再是与我无关的、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符咒,而是我能去理解、去掌握的智慧。恐惧的灵,曾如影随形地压迫我,如今已被儿子的心所取代,让我能自然地呼唤:“阿爸,父啊。”
当然,旧日的习惯还会偶尔冒头。听到大声的呵斥,我仍会下意识地瑟缩;面对丰盛的食物,我第一反应仍是自卑与退缩。但每当我摸到手指上的戒指,感受到那实实在在的、象征权柄与归属的圆环,我的心便渐渐安定下来。我不再回到那懦弱无用的“小学”之下,不再想把自己重新套进那已然破碎的奴仆轭中。
如今,我行走在这宅院里,脚步是踏实的。我知道我是谁。我不是靠着行为称义,不是靠着守全律法得产业——那原是我永不可能做到的。我站在这恩典之地,只因父亲的呼唤与收纳。这恩典,如此真实,比罗马的铺石路更实在;这名分,如此牢固,比海边的磐石更坚稳。我是儿子。直到永远。
夜风吹过庭院,带着自由的气息。那风穿过我曾躲藏的廊柱,如今也轻柔地拂过我的窗棂。我闭上了眼,心中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、静谧的平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