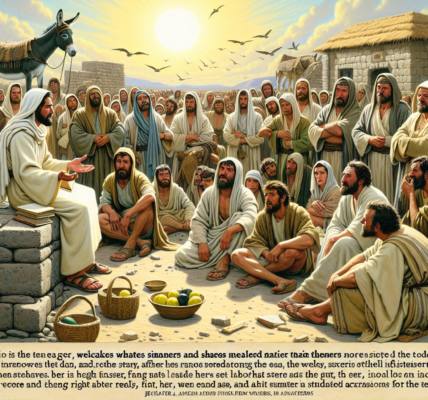帳棚裡最後一點暖意,也隨著雅各的離去而消散了。約瑟伏在父親冰涼的面容上,許久沒有抬頭。埃及細膩的亞麻裹屍布,薰著沒藥與沉香濃得化不開的香氣,卻蓋不住那股屬於漂泊者、屬於迦南塵土、屬於神應許之地的氣味。那是父親身上一直帶著的,曠野與羊群、汗水與誓言交織的氣味。如今,這氣味正一點一點,從這華美的停屍帳幕裡流逝。
哀哭的日子長得彷彿沒有盡頭。埃及的術士與祭司們以精準的禮儀履行一切,刀割面頰的祭司,排成長列的職業哭喪者,他們的悲聲整齊劃一,卻進不到約瑟心裡。他心裡翻騰的,是另一種惶恐。父親不在了。那根維繫著、鎮壓著、調和著這個家族微妙平衡的巨柱,轟然倒塌。他聽見帳外哥哥們壓低的交談,偶爾幾個詞語碎片般飄進來:「……父親死了……」「……約瑟會不會……」「……從前的罪……」
他閉上眼,幼年時多夢的夜晚又浮現眼前。那件彩衣被撕裂,染上羊血,哥哥們冷漠或狂怒的臉,坑底的黑暗,以及米甸商人銀錢的叮噹響。那麼多年了,他以為自己早已放下。他在埃及的權勢中,在法老的恩寵裡,在豐年與荒年的操勞間,將那些記憶打磨成了光滑的、不再傷人的石子,深深埋藏。可父親一闔眼,所有埋葬的東西都開始鬆動。他這才驚覺,那不僅僅是他的記憶,也是哥哥們的。他們的記憶裡,有更多的恐懼。
葬禮的隊伍從歌珊出發,浩大得令埃及人也側目。法老的臣僕、埃及的長老、戰車、馬兵,簇擁著那具用埃及最高技藝防腐、卻要歸葬迦南的軀體。過約旦河時,約瑟看著渾黃的河水,恍然想起另一個過河的人——他的祖父亞伯拉罕。也是這樣,帶著應許與未知,從大河那邊過來。如今,他們要將承載應許的父親,送回河那邊去。亞達的禾場上,七日晝夜不息的哀哭,迦南人看了都說:「這是埃及人一場極大的哀哭。」約瑟聽見這話,心裡湧起複雜的滋味。他們哭的,豈是一個埃及的尊貴人物?他們哭的,是他們的父親雅各,是那個在毗努伊勒與神摔跤、從此人就瘸了,卻也更名叫以色列的人。
葬禮結束,眾人回到埃及。現實的空白驟然顯現。哥哥們聚在一處,竊竊私語,目光躲閃。終於,他們推舉出一人,或許是猶大,來到約瑟面前,伏地說道:「父親在未死以先吩咐說:『你們要對約瑟這樣說:從前你哥哥們惡待你,求你饒恕他們的過犯和罪惡。』如今求你饒恕你父親之神的僕人的過犯。」
話說得婉轉,援引了父親的遺命。但約瑟聽出了那弦外之顫音。父親真的說過這話嗎?或許有,或許只是哥哥們在極度驚懼中的託辭。他看著眼前這些頭髮也已花白的兄長,他們額頭緊貼著華麗埃及地磚的樣子,與當年那個趾高氣揚將他賣掉的青年們,重疊又分開。時間在他們臉上刻下了深深的溝壑,裡面積滿了懊悔與後怕。
約瑟的眼淚毫無預兆地湧了出來。不是為了父親,是為了他自己,也為了他們。他叫他們近前來。他們遲疑地挪近,肩膀緊繃,準備承受遲來數十年的審判。約瑟開口,聲音因哽咽而沙啞:
「不要害怕。我豈能代替神呢?」
帳幕裡靜極了,只有尼羅河遠處隱約的風聲。哥哥們抬起頭,不敢相信。
「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,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,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,成就今日的光景。」他緩緩說著,每一個字都像從很深的井裡打撈上來,帶著記憶的濕重與歲月的澄澈。「現在你們不要害怕,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婦人孩子。」
他不再是以埃及宰相的身份說話,他是一個弟弟,一個同樣在命運激流中跌撞浮沉、最終看見了神那雙隱秘之手的凡人。他安慰他們,用親切的話語,一遍又一遍,直到他們臉上緊繃的肌肉鬆懈下來,直到他們眼中那積存數十年的恐懼,漸漸融化,化作另一種更洶湧的熱流,奪眶而出。
往後的日子,約瑟和他的父家,依舊住在歌珊。他活了很久,見到以法蓮的第三代子孫,也見到瑪拿西的孫子瑪吉的兒女。他老了,躺在埃及柔軟的床榻上,周遭是尼羅河三角洲豐腴的氣息。可他知道,自己的根不在這裡。他叫了子孫們來,氣息已弱,話語卻清晰:
「我要死了,但神必定看顧你們,領你們從這地上去,到他起誓所應許給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」他讓他們把手放在他腿下,起誓一定要將他的骸骨帶上去。那不是埃及式的、追求永恆不朽的誓言,而是一個寄居者的、指向未來歸宿的約定。
他最後一次閉上眼,不是作為威嚴的宰相,而是作為雅各的兒子,作為那個曾擁有彩衣、曾做過異夢、曾被丟在坑中、也曾站在法老面前的約瑟。他們用埃及的方法薰了他的身體,把他收殮在棺材裡,停在歌珊某處。那棺材在未來的四百年裡,會成為一個沉默的見證,提醒那些為奴的子孫:應許之地不是傳說,我們終要回去。而約瑟的骸骨,比任何財寶與權杖都更有力量,因為它裡面封存的,不是死亡,是一個確鑿的、等待應驗的盼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