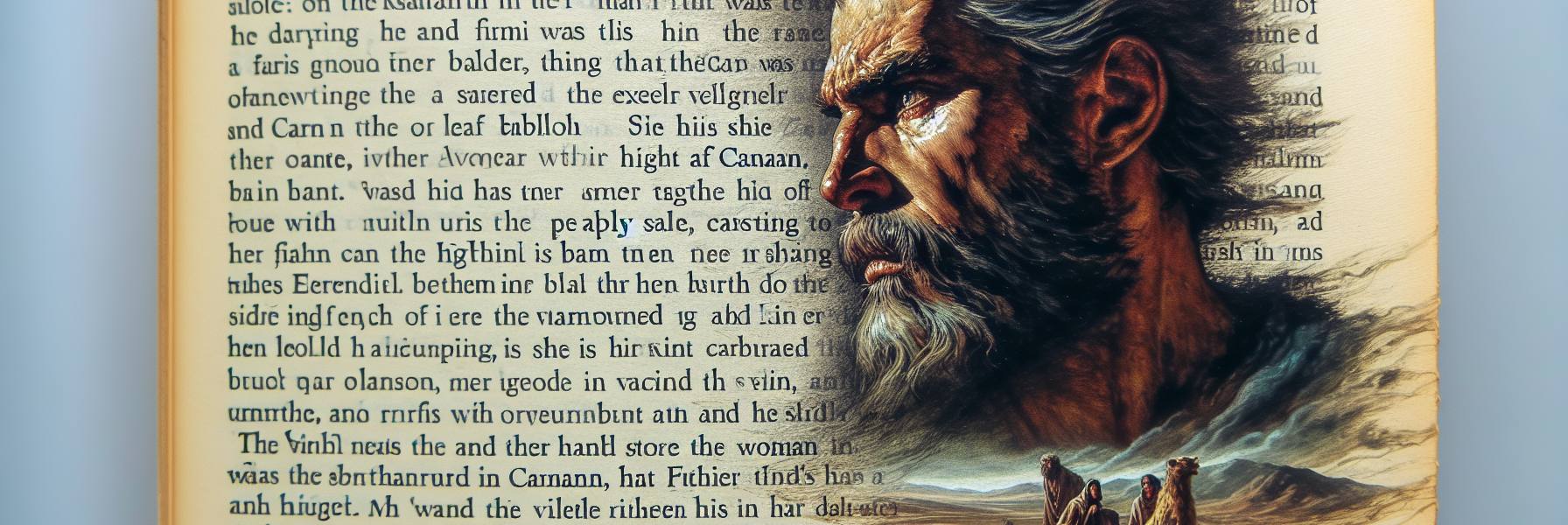窑匠街的尘土在午后斜阳里浮沉,像极了烧陶时扬起的细灰。以西结坐在门槛上,汗湿的麻衣粘着背脊,他却浑然不觉。忽然,一阵燥热的风卷过街角,刮起地上的碎陶片,哗啦啦响成一片。他阖上眼,再睁开时,耶路撒冷不见了,眼前只有一片荒场。
那是个阴沟旁的弃婴。脐带还未剪净,混着血污和泥浆,在小坑洼里蜷成皱皱的一团。没有裹布,没有盐水擦身,连啼哭都微弱得像野猫哀鸣。她就那样被扔在野地里,等着被日光晒干,或是被野狗叼去。以西结感到胸口发紧——那不是怜悯,而是一种更深的、近乎窒息的熟悉感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,婴孩竟没死。她躺在自己的血污中踢动细腿,直到有脚步声踏过荒草。那身影俯下身,不是拾荒的乞丐,而是一位过路者。他停住了,说了一句奇怪的话:“你正活在血中。”声音里没有嫌弃,倒像在陈述一个事实。他伸出双手,不是掩鼻远离,而是将她抱起。
弃婴长大了,像河滩边的芦苇,抽得飞快,却瘦伶伶的。胸部微微隆起,头发结成毡片,仍是赤身露体。过路者又来了,这次他展开衣襟,将她裹住。布帛摩过皮肤的触感,让她第一次发起抖来。他用手覆住她的血,那血就止住了。他用清水给她沐浴,盐粒擦在身上刺痛,她嘶嘶吸气,他却不停手。洗毕,他给她抹上油膏,香气陌生又浓郁。
然后是衣裳。细麻的内袍,绣花的斗篷,海狗皮的靴子——件件都过于隆重,像给公主穿戴。他又用首饰装扮她:鼻环、耳坠、金链、珍珠。最后,一顶精金的冠冕压上她刚刚梳通的头发,沉甸甸的。她站在水洼前照,里面的人影华美又陌生,只有那双眼睛,还留着阴沟旁野狗般的惊慌。
“你全然美丽,”过路者说,他的目光像秤,“是我所赐的荣美。”
他们立了约。他给她细面、蜂蜜和油。她吃足了,身体丰润起来,皮肤透出光泽。她的名声响彻列国,因那赐她华美之主的缘故。她渐渐忘了坑洼里的血污,忘了野地里的寒风,甚至忘了那双将她抱起的手上,粗粝的茧。
她开始信赖自己的美丽。那冠冕,那锦缎,仿佛本就是从她血肉里长出来的。她将金饰熔了,铸成高台,在上面与每一个路过的客商行淫。她拿华美的衣裳铺在青翠的松树下,当作拜偶像的褥子。她甚至将儿女——那过路者所赐的产业——牵去,穿过火,献给哑巴偶像作祭物。
“你还不满足吗?”以西结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荒场上空响起,干裂如久旱的泥土,“你竟将我所给的,去换那不能饱足的外邦香料,将我的金银,去造那可憎的偶像!”
那华美的妇人,此刻正倚在街口,向亚扪人、非利士人、亚述人、迦勒底人媚笑。她付钱给他们,倒贴妆奁,求他们近前来。她在各路口筑坛,将属于过路者的香气,烧给别样的神。
荒场忽然暗了。聚集的不是云,是黑压压的、她曾谄媚过的列国。亚述人先来,剥去她的外袍。非利士人在旁嗤笑。迦勒底人用刀划开她的刺绣,夺走孩童。最后,他们将她剥尽,赤身露体,像最初躺在血污里的那日。他们用石头砸她,用剑劈砍,用火烧她的房屋。华美的宫殿坍倒,高台成了瓦砾堆,精金的冠冕被人踩进泥里。
荒场寂静。只有烧焦的木头发出的毕剥声,和乌鸦的啼叫。
许久,也许是一瞬,那过路者的声音再次响起,低得像从地底传来:“然而我要追念你幼年的盟约,也要与你立定永约。”
以西结睁开眼。窑匠街的斜阳已转为暗金,陶轮在隔壁吱呀转动。他脸上冰凉,一摸,竟是未干的泪。他知道,这不是一个比喻,而是一道伤口,一道从耶路撒冷心脏直划到他肋骨下的、鲜红的伤口。风还在吹,卷起的尘土里,他仿佛看见一丝极微弱的、金子的闪光,埋在厚厚的灰烬之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