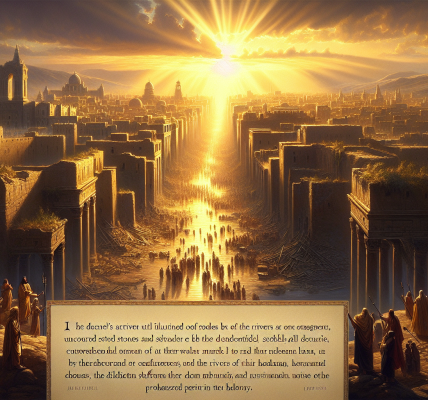七月将尽,米斯巴的暑气依然黏稠。凉棚下的无花果已经干瘪,几只苍蝇嗡嗡地盘旋。基大利擦了擦额头的汗,对坐在对面的约哈难摆摆手:“你不必多疑。以实玛利是王室之后,他来投奔,我若猜忌,怎能叫流散的人心安?”
约哈难的手指在粗陶碗边摩挲,碗底还剩些浑浊的酒。“总督,”他的声音压得很低,“尼探雅的儿子带着十个人,从亚扪王那里来。刀鞘上的皮扣,磨得发亮。”
基大利笑了。那笑容里有种令人不安的宽厚,像是早已看穿命运,又像是闭目不看深渊。“我们既归顺巴比伦,就当以诚信待人。明日我设宴款待他们,你也来。”
夜里起了风,吹得橄榄树林沙沙作响。以实玛利站在院子西侧的井边磨刀,石头与铁刃摩擦的声音短促而均匀。他的两个手下在阴影里分食一块干饼,没有说话。月光照见以实玛利半边脸,颧骨高耸,眼窝深陷——那是王族血脉在流亡中刻下的印记。他曾是王室贵胄,如今却要对着一个平民出身的省长弯腰。刀锋映出一弯冷月。
次日正午,宴席设在总督府院内的石榴树下。饼是麦饼,酒是土酿的酒,还有几盆炖豆子。基大利坐在首位,以实玛利在他右手边,十个人分散坐着。约哈难来了,坐在离门口最近的席位上,手始终没离开腰间的短刀。
谈话是零碎的。说到北地的收成,说到几户从摩押回来的家族。以实玛利的话很少,只是附和,偶尔抬起眼睛看看基大利。他的眼睛很平静,平静得像亚扪高原上的死海。
吃到一半,基大利举起酒杯:“愿这地得享太平……”
话音未落,以实玛利突然站起,手中的陶碗摔在地上,发出闷响。几乎同时,那十个人像豹子一样扑了上来。基大利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,只觉得胸口一凉,低头看见一截铁刃从背后穿出,血顺着总督袍子的紫色镶边往下淌。他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却只吐出一口血沫,身子歪倒在食案上,压翻了盛豆子的陶盆。
院子里炸开了。总督的护卫拔出刀,但太迟了。以实玛利的人已经控制了门口。刀光,惨叫,倾倒的桌椅,溅血的石榴树。约哈难踢翻面前的桌子,挡住劈来的刀,撞开侧面的小门滚了出去。他听见身后自己仆从的哀嚎,不敢回头,拼命往城西跑。
杀戮只持续了一炷香的时间。以实玛利站在院子中央,踢了踢基大利的尸体。“搜,”他的声音不大,“活口一个不留。”
但命运总是讽刺。就在他们清洗总督府的时候,从示剑、示罗、撒马利亚来了八十个人,胡须剃了,衣服撕裂,头蒙灰尘——是往耶路撒冷圣殿废墟献素祭和乳香的朝圣者。他们牵着一头驴,驴背上驮着麦饼和干果,还不知道米斯巴已变天。
以实玛利擦着刀上的血,听见城门守卫来报,眼里闪过一道光。“去迎接,”他说,“要哭泣着去迎接。”
他换了件沾血不多的外袍,带着人出城,遇见那支朝圣的队伍。他捶胸顿足,泪流满面:“基大利总督……请你们进去相见。”
那些虔诚的人跟着他进了城。一进总督府院子,看见满地尸首,血浸透了泥土,转身想逃。门已经关上了。以实玛利的人像砍柴一样砍倒他们。只有十个人跪地哀求:“我们田里有埋藏的麦子、油和蜜,饶我们性命,都献给你!”
以实玛利摆了摆手,让人把这十个活口捆了。其余七十具尸首,连同基大利和犹大人的尸体,都被扔进院子里那个巨大的蓄水池——那是亚撒王当年为防备巴沙所挖的,如今池里没有水,只有层层叠叠的躯干、手臂、空洞望天的眼睛。
黄昏时分,以实玛利掳走了城中剩下的人,包括王的女儿们——那些西底家留给基大利照看的柔弱女子。队伍蹒跚向北,要在亚扪去。
但约哈难逃出去了。他带走了残存的军长和士兵,也带走了愤怒和恐惧。他们在基遍的水泉边追上以实玛利的队伍。被掳的人看见救兵,呜咽着调头跑来。以实玛利只带着八个人,趁乱钻进了东边的山丘,消失不见。
约哈难清点人数,清点伤痕,清点死去朝圣者留下的那点麦饼和乳香。女人们在哭,孩子们在发抖。他站在基遍的水泉边,看着水面上漂浮的几片无花果叶子,忽然觉得浑身冰冷。
米斯巴的惨案像一道裂开的伤口,暴露在迦南的烈日下。基大利相信的和平,以实玛利追求的复仇,朝圣者怀抱的虔诚——都在那个蓄水池里混成了同一片黑暗。而他们这些剩下的人,该往哪里去呢?没有人说话。只有水泉还在流淌,孜孜不倦,仿佛在洗刷怎么也洗不掉的血腥。
远处,亚拿突的山峦在暮色中变成青紫色。耶利米的话,此刻才像迟来的钟声,一声声敲在约哈难的心上:“倚靠人血肉的膀臂,那人必受咒诅。”可人若不倚靠自己的膀臂,在这破碎的世上,又能倚靠什么呢?他蹲下身,双手捧起泉水,水从指缝间漏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