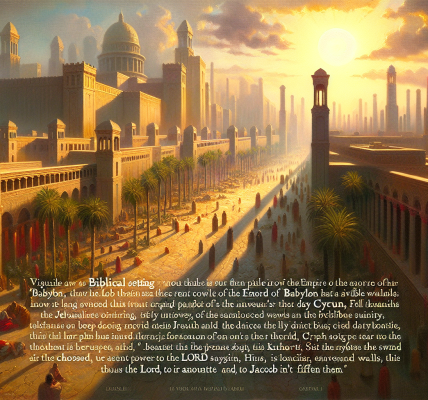约押站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,橄榄木的窗棂在他手中微微发烫。正午的阳光把石头城墙晒出热浪,远处有商队驮着香料缓缓而行。他刚读完王从拉巴送来的泥板文书,指节因用力而发白。
“亚扪人的王死了。”他对身旁的亚比筛说,声音像是从磨石间挤出来的。
他们的王大卫曾与亚扪先王拿辖有过盟约。如今新王哈嫩继位,大卫差遣臣仆前去吊丧。约押记得那几个使臣出发时的模样——穿着细麻布长袍,额上抹着橄榄油,带着乳香与没药作为丧礼。谁料不到半月,他们竟满脸须发尽毁、袍子被割去下半截地逃回来。亚扪人竟将他们当作奸细,剃去他们半边胡须,割破衣袍露出下体。
“这是把以色列全军的脸面按在泥里踩。”亚比筛握紧腰间的刀,铜制的刀柄被晒得烫手。
果然,哈嫩花了一万他连得银子,从米所波大米、亚兰、玛迦雇来三万二千辆战车。消息传来时,橄榄山的夜风正带着无花果的甜香。约押看见王在圣幕前跪了一整夜,清晨起身时,袍角还沾着露水。
两军在米底巴平原相遇时,正逢旱季最酷烈的时节。亚扪人在城门前列阵,雇来的亚兰车兵在郊野拉开阵势,铜甲反射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。约押把自己的精兵分成两股,他对亚比筛说:“若亚兰人强过我,你就来救我;若亚兰人强过你,我就去救你。”
那是他生平最漫长的一个清晨。冲锋时马蹄踏起的尘土带着血腥味,被割断的缰绳像蛇一样在沙地上扭动。有个亚兰车兵的长矛擦过他的肩甲,青铜与铁摩擦出刺耳的声响。他闻到死亡的气息——不是腐臭,而是铁锈混着汗水的咸腥。
忽然东边扬起新的烟尘。亚比筛的部队像山洪般冲破亚兰人的右翼,那些穿着彩袍的雇佣兵开始后退。约押记得有个年轻的亚兰军官,在战车倾覆时仍死死握着军旗,直到以色列士兵的刀锋没入他的胸膛。
败退的亚兰人逃到更北的大马士革。数月后,他们带着新的战车卷土重来。这次率领他们的是朔法,据说他能用铜杖在沙地上画出整个新月沃地的地图。两军在希兰结相遇时,旷野的风滚草正开出细小的黄花。
那场战役持续到月升时分。大卫王的将领们第一次见到亚兰人用双马战车组成楔形阵,车轴上的镰刀在暮色里闪着寒光。直到月亮升到头顶,亚兰的元帅才在乱军中被斩落。他的铜盔滚进干涸的河床,惊起几只夜栖的沙鸡。
战后清理战场时,约押在破损的战车里找到一只银制的水囊。拔开塞子,里面还留着半壶发馊的葡萄酒。他想起那些被羞辱的使臣,想起他们用破损的衣袍遮住脸庞的模样。风从以东的方向吹来,带着死海盐粒的苦涩。
班师回耶路撒冷的路上,他们经过一片石榴园。熟透的果实裂开口子,露出晶莹的籽实。有个士兵摘下一颗递给约押,他掰开果实时,深红的汁液顺着指缝流淌,像极了那些染红米底巴平原的鲜血。
在圣殿的台阶前,王亲自为得胜的将士斟酒。酒是迦密山产的陈年葡萄酿,在陶瓮里存放了七个丰年。约押举杯时看见王眼角新添的纹路,忽然明白这场胜利不过是更大风暴的前奏。晚祷的号角声从锡安山传来,惊起群群归巢的野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