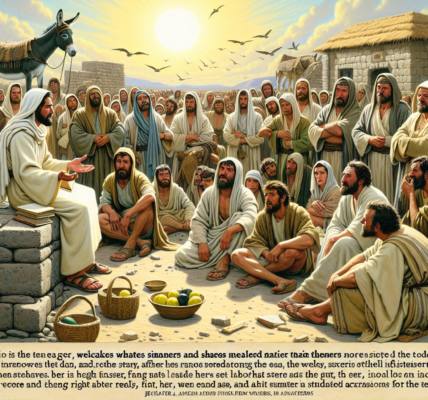黄沙被风卷着,贴着帐棚的毡子边打旋。撒莱坐在内室,手里捻着一缕羊毛,捻得紧紧的,指节都有些发白。帐外传来女人们打水的说笑声,是埃及的口音,清脆,带着点儿她学不来的利落。那是夏甲的声音。羊毛粗糙的触感还在指尖,但撒莱的心已经飘远了,飘到这十年来每一天、每一个无望的清晨与黄昏。应许如同天上的星辰,清晰闪耀,却遥远得令人胸口发疼。亚伯兰的头发,已渐渐染上灰白的风霜。她的腹中,却依旧只有一片沉寂,像死海的水,不起微澜。
一个念头,不知是从何时开始滋长,像夜间悄然爬过沙地的蝎子,等她察觉时,那毒尾已悬在心头。是丁,律例风俗如此,婢女所生,可算在主母膝下。这念头起初让她惊惶,仿佛亵渎了那立约的神。可日复一日,应许的迟延与腹内的空旷较量着,终于将那惊惶磨成了某种坚硬的、近乎破釜沉舟的决心。它不是喜乐,而是一种苦涩的权宜。
她对亚伯兰说这话时,没有看他眼睛,只盯着面前那碗微微晃动的羊奶。“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。”她的声音干涩,像晒裂的陶片,“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,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”话出了口,便在帐内沉甸甸地坠着。亚伯兰沉默了很久,那沉默里有叹息的重量。他没有反驳。应许是给他的,道路却常是这样模糊难辨,满是人的痕迹。
事情就这样成了。并不在欢愉中,倒像完成一桩肃穆而无奈的仪式。夏甲被领进亚伯兰帐中的那夜,撒莱独自躺在自己的毯上,听着远处隐约的驼铃,心里空落落的,仿佛亲手将一把沙子捧起,却不知风要把它吹向何方。
变化来得很快,快得让撒莱措手不及。夏甲不再是那个低眉顺目、手脚勤快的埃及使女了。她的腰身尚未明显粗壮,但那微微挺起的姿态,那眼角眉梢偶尔掠过的一丝神气,像水底的暗影,清晰可辨。起初是些小事:吩咐她做的事,应得慢了;打来的水,似乎也没从前那般清冽甘甜。直到那一天,撒莱分明看见,夏甲摸着尚且平坦的小腹,对着几个年轻的婢女,嘴角弯起一个极淡、却极刺人的弧度。
撒莱感到一股火,从心底最寒凉处猛地烧上来。那不是愤怒,是崩塌。她以为可以藉此修筑的,如今却成了最先坍塌的高墙。她找到亚伯兰,话像烧红的石子往外迸:“我因你受了屈辱!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,她见自己有了孕,就小看我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!”
亚伯兰脸上满是倦意,还有更深沉的、对两个女人处境的无能为力。他挪开目光,看着帐外无垠的沙地,声音疲软:“你的使女在你手下,你可以随意待她。”他把权柄还给她,却也把那份撕裂人心的重担,全然卸回她的肩头。
于是撒莱收起了最后一点犹疑。她待夏甲严苛起来。不是打骂,而是那种冰冷入骨的、无时不在的漠视与轻蔑,像一件湿冷的衣裳紧紧裹住夏甲。往日的和颜悦色不见了,每个眼神都带着秤,称量着夏甲僭越的分量;每句吩咐都像鞭子,抽打在那刚刚萌芽的骄傲上。帐棚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,只有两个女人的沉默在角力。
夏甲终于受不了了。那曾让她自觉高贵的腹中生命,此刻却成了主母眼中钉刺。一个清晨,天色还未大亮,她什么都没拿,只穿着平日衣裳,一头闯出了帐幕,朝着南边,朝着书珥的方向——那是通往埃及,通往她故土的大路——头也不回地奔去。旷野的风立刻包裹了她,干燥,粗粝,带着自由而残酷的气息。她走了很久,直到日头酷烈,口干舌燥,才在一处小小的水泉边瘫软下来。四下只有嶙峋的石头和无穷无尽的沙土,刚才那股决绝的勇气,被这荒凉一泡,渐渐化作了巨大的茫然与恐惧。她摸着肚子,那里微微的悸动此刻只让她感到无边的孤独。她伏在地上,起初是哽咽,后来便放声痛哭,哭声被旷野吞吃,只剩微弱的回响。
就在这绝望的泣声中,她听见一个声音,不是风吹过石隙的呜咽,是清晰、沉稳,直透心底的言语:“撒莱的使女夏甲,你从哪里来?要往哪里去?”
她惊惶抬头,四下并无人影,只有烈日下晃动的热浪。但那临在感如此真切,压迫着她的呼吸。
“我从我的主母撒莱面前逃出来。”她颤声回答,仿佛那发问者就在眼前。
那声音又说:“你回到你主母那里,服在她手下。” 这话让她心一沉,如同判决。但接下来的话,却像暗夜中忽然点亮的火把:“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,甚至不可胜数。” 接着,那声音述说更具体的应许:她怀的是个儿子,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,因为耶和华听见了她的苦情。这儿子将会像野驴,他的手要攻打人,人的手也要攻打他,他必常与他的众弟兄为敌。
夏甲怔住了。旷野的风似乎静止了。神竟看见了她?这卑微的、逃亡的使女?一种前所未有的战栗与敬畏抓住了她。她不再觉得孤单,那腹中的生命,忽然被一道无法言喻的光照亮。她几乎脱口而出,给那对她说话的神起了一个名字:“你原来是‘看顾人的神’!” 因为她实实在在地说:“在这里,我也看见了那看顾我的吗?”
泉水仍在汩汩流淌,清亮照人。她喝足了水,洗去脸上的泪痕与沙尘。回去的路,似乎不再那么可怕。她记下了那地方,称那井为“庇耳拉海莱”,意思是“那看顾我的永活者之井”。这井的位置,后来人说,就在加低斯和巴列之间。
夏甲转身,循着来时的足迹,一步步往回走。步伐沉重,却有了方向。她回到亚伯兰的帐棚,回到撒莱面前,默默地,重新拾起使女的身份。只是她的眼瞳深处,有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,像旷野里被星光洗过的石头,沉静而坚韧。
时候到了,夏甲生下一个儿子。亚伯兰按照那在旷野所闻的吩咐,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。产帐内婴儿的啼哭声嘹亮,传出很远。亚伯兰抱着这头生的儿子,八十六年的人生风霜刻在他脸上,此刻漾开的是复杂难言的涟漪——有喜悦,有感慨,有对那更遥远应许的茫然期盼。撒莱站在不远处看着,心中那股苦毒与空缺,并未被这哭声填满,反而像被衬得更深了。帐外,黄沙依旧,风声不息。应许的故事,人的轨迹,在此刻交织成一个结,紧紧系在这新生儿的腕上。旷野的预言,如同一个烙印,悄无声息地,落在了这个家庭未来的命途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