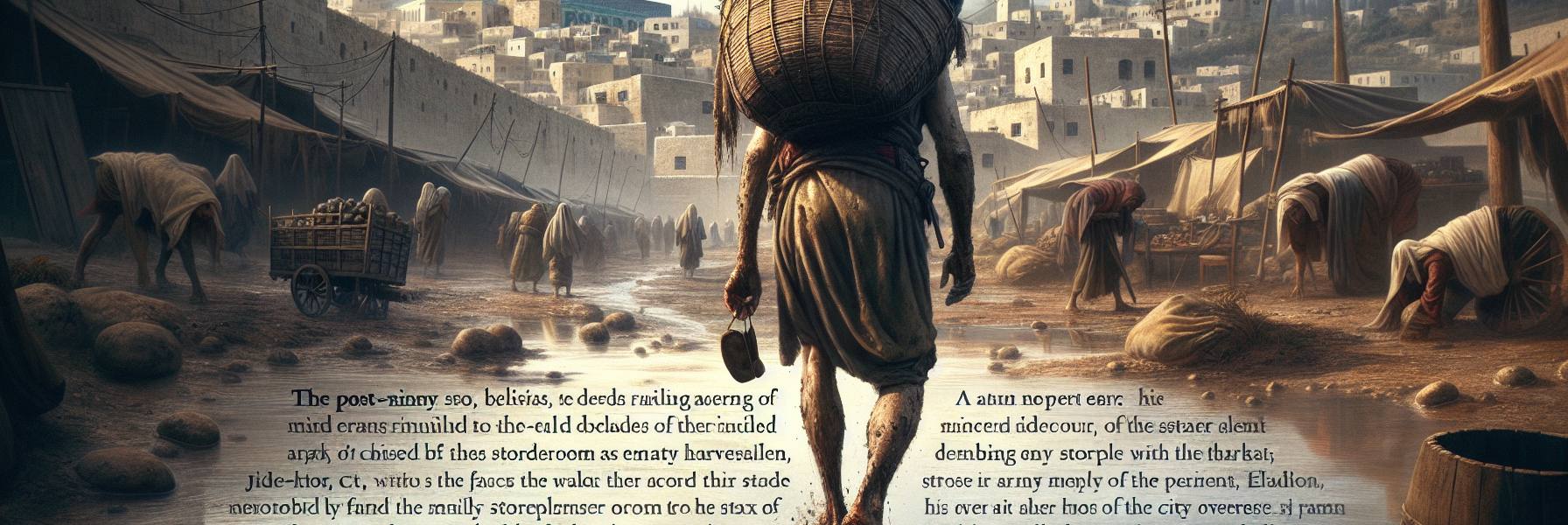城是醒着的,即使是在这样的时辰。巷子深处传来竹帚划过青石板的声音,沙,沙,沙,单调而固执。阿磐靠在冰凉的土墙边,看着那声音的来处——一个佝偻的影子,在将明未明的天色里,缓慢地移动。他摸了摸怀里,只剩下几枚被汗水浸得发亮的铜钱。昨日的工钱,大半又喂了那个挂着“濟世”匾额却眼神闪烁的郎中。妻子的咳嗽,像破风箱一样,夜夜撕扯着这个家。
他抬起头,天际有一线惨白,像一道刚刚结痂的伤口。指望谁呢?他想起前几日码头上管事拍着他肩膀说的话:“好好干,年下给你加一份赏钱。”那笑容里的敷衍,如同河面上浮着的油污,光亮而虚假。他也曾将微薄的指望寄托在巷尾那间香火鼎盛的小庙,奉上最后的几文,求来的签文却语焉不详。人间的承诺,仿佛雨季墙根的青苔,看着鲜亮,一碰就化成滑腻的虚无。他的心,像被这晨雾浸透了的麻布,沉甸甸,冷冰冰。
阿磐挪动了一下僵直的腿,准备去等今天第一趟活计。这时,一阵不同寻常的声音传来,不是竹帚声,而是歌声。嘶哑,苍老,甚至有些走调,却有一种奇异的穿透力,从那扫街老人的方向飘来。阿磐听不懂全部的词句,但那断断续续的调子,裹挟着几个清晰的字眼,撞进他的耳朵:
“……你們不要倚靠君王,不要倚靠世人,他一點也不能幫助。他的氣一斷,就歸回塵土;他所打算的,當日就消滅了……”
阿磐愣住了。这话像一根冰冷的针,猝不及防地刺破了他心里那些肿胀而无望的期待。君王?世人?他哪里够得着。他倚靠的,不过是管事一句空话,郎中一剂苦药,泥塑木雕一个空洞的眼神。这些,不都如同那歌中所说,气息一断,便归尘土,当日打算,转眼成空么?他倚靠的,原来尽是些要归于尘土的东西。一种深刻的疲惫,比身体的劳累更甚,淹没了他。
老人的歌声没有停,在扫帚的节奏间隙里,顽强地生长着,转向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调子。那声音依旧沙哑,却仿佛被一股内在的热力点燃:
“……以雅各的神為幫助、仰望耶和華—他神的,這人便為有福!耶和華造天、地、海,和其中的萬物;他守誠實,直到永遠。他為受屈的伸冤,賜食物與飢餓的。耶和華釋放被囚的……”
阿磐的脚步钉在了原地。这些话,他似乎在童年遥远的记忆里听过,在母亲哄睡的含糊低语里,后来被生活的尘土深深掩埋。此刻,它们被这扫街老人用最粗粝的方式唱出,却仿佛带着千斤的重量。造天、地、海的神?那太远了。但后面的话,却像火光一样,瞬间照亮了他漆黑的心室:**為受屈的伸冤。賜食物與飢餓的。釋放被囚的。**
受屈的?他看着自己生满老茧的手。饥饿的?他腹中的空洞感从未真正消失。被囚的?他被困在这条巷子,这场疾病,这种日复一日没有尽头的挣扎里,难道不是另一种囚笼吗?
老人扫到了他的近前,并没有看他,依旧专注于脚下的尘土,歌声却如同自语,又如同宣告:“耶和華開了瞎子的眼睛;耶和華扶起被壓下的人;耶和華喜愛義人。耶和華保護寄居的,扶持孤兒和寡婦……”
瞎子的眼睛?阿磐忽然觉得,自己或许才是那个瞎子,只看得到眼前的窘迫,看不见别的。扶持孤儿寡妇?他想起病弱的妻子和面黄肌瘦的稚儿,他们不正像风中瑟瑟的苇草么?
天色又亮了一些,青灰色的光涂抹在瓦檐上。老人扫完了这一段,扛起竹帚,慢慢走向巷子的另一头。那不成调的歌声渐渐远去,最后几句却格外清晰,顺着风送过来:
“……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。耶和華要作王,直到永遠!錫安哪,你的神要作王,直到萬代!你們要讚美耶和華!”
歌声消失了,只有“你們要讚美耶和華”那几个字,像几颗温润的石子,投入阿磐死水般的心里,漾开一圈细微却无法止息的涟漪。恶人的道路弯曲?他不知道。但他仿佛看见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,不是倚靠那终归尘土的人与物,而是朝向那位守诚实直到永远、为受屈者伸冤、扶起被压下者的……神。
城彻底醒了。人声、车马声开始嘈杂。阿磐深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,那空气里似乎有了一丝不同的味道。他依然要去为今天的口粮奔波,妻子的药罐依然等着银钱。什么都没有改变。但又好像,一切都不同了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,那手里依然空空,心里那个沉甸甸的、湿冷的麻布结,不知何时松开了。一种陌生的、微小的力量,从很深的地方生出来。
他迈开步子,汇入渐渐汹涌的人流。远处的江涛声隐隐传来,永恒而有力,如同那首歌里所唱的,直到万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