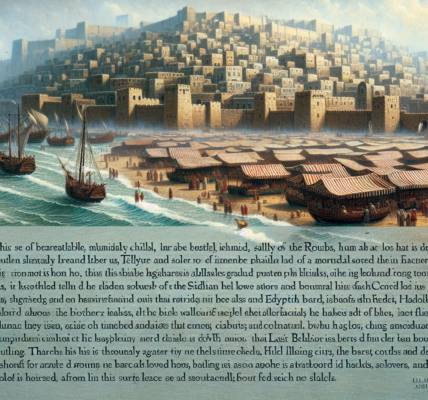伯大尼村口的那棵老无花果树,叶子已经卷了边,蒙着一层从耶路撒冷路上扬过来的细白尘土。拉撒路家的院子里静得出奇,只有几只麻雀在啄食昨日宴席散落的面包屑。屋里传出一种低沉的、连绵不绝的哭泣声,不是嚎啕,而是一种被痛苦浸透了的、疲惫的呜咽,像是从地底渗出来的水。
马大听见脚步声就出来了。她围裙上沾着炉灰,眼睛又红又肿,像两颗熟透了的李子。“主啊,”她的声音沙哑,带着一种责备般的委屈,“你若早在这里,我兄弟必不死。”话说出口,她似乎又后悔了,手指绞着粗布围裙的边缘,补了一句,像是为自己也为那缺席的人找一个台阶:“就是现在,我也知道,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,上帝也必赐给你。”
耶稣看着她,目光沉静,仿佛能看透她心里那团理不清的结——信,却又含着怨;盼望,却又被死亡冰冷的现实重重压着。“你兄弟必然复活。”他说。
马大点点头,那是一种属于敬虔人的、公式化的点头,是她在会堂里听惯了应许之后的条件反射。“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,他必复活。”她说着,眼泪又滚下来,不是为了那遥远的、属于所有人的应许,而是为了此刻屋里那具没有生息的、正在渐渐冰冷的身躯。
“复活在我,生命也在我。”耶稣的话不大,却像一块石头投入死寂的潭水,惊起的不是涟漪,而是某种更深邃的迴响。他看着她迷惑的脸,风拂过他额前的发丝,带着旷野与路途的气息。“信我的人,虽然死了,也必复活。凡活着信我的人,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?”
马大怔住了。这话超越了会堂里拉比的讲解,超越了律法书卷上工整的字句。它直接、强烈,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柄,刺破了她悲伤的麻木。她张了张嘴,那句熟稔于心的信仰告白,此刻说出来却有了全新的、近乎战兢的重量:“主啊,是的。我信你是基督,是上帝的儿子,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”
她转身进去,脚步有些仓促,在妹妹马利亚耳边低声说了什么。马利亚立刻站起来,脸上的泪痕还没干,就急急地往外走。那些陪着她哀哭的犹太人也跟着,以为她是要去坟上痛哭。
马利亚看见耶稣,就俯伏在他脚前,说的和姐姐一样的话,但语气全然不同。那里面没有马大那种带着行动的焦躁,只有被悲伤彻底击垮后的柔软与全然依赖:“主啊,你若早在这里,我兄弟必不死。”她说完,便只是哭泣,肩膀轻轻耸动,泪水打湿了耶稣脚上的尘土。
耶稣看着她,看着周围那些陪哭的人一张张真实或应景的悲戚面孔,又望向那个封着石头的墓穴方向。他心里忧愁,又甚悲叹。“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?”他问,声音里有一种压抑的沉重。
他们说:“主啊,你来瞧。”
耶稣哭了。
这短短的四个字,像一道闪电,照亮了整个场景的深渊。不是作态的哀哭,不是先知的宣告,只是一个挚友的眼泪,温热、真实,顺着脸颊流下来。旁边的人看见了,有的低声说:“你看他何等爱这人。”也有的,永远不乏这样的人,带着一丝挑剔的疑惑:“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,岂不能叫这人不死么?”
他们来到坟前。那是个洞穴,前头滚着一块大石头,封得严严实实,隔绝了生与死两个世界。坟墓周围弥漫着死亡四天后那种特有的、不容错辨的微甜腐败气息,混杂着香膏和泥土的味道。几只苍蝇嗡嗡地绕着。
“把石头挪开。”耶稣说。
马大,那个刚才还宣告信心的马大,此刻又被现实的、可怖的气味拉了回去。“主啊,”她急忙拦住,脸上带着近乎惊恐的务实,“他现在必是臭了,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。”
耶稣转脸看她,眼角的泪痕还在,但目光清亮如炬:“我不是对你说过,你若信,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么?”
人们面面相觑。几个壮实的乡邻走上前,抵住那块冰冷沉重的大石头,闷哼着用力。石头摩擦地面,发出粗糙刺耳的声响,缓缓滚开。一个幽深的、黑暗的洞口露了出来,那股气味更浓了,人群微微骚动,向后退了半步。
耶稣举目望天。正午的阳光有些刺眼,他眯起眼,祷词简单而直接:“父啊,我感谢你,因为你已经听我。我也知道你常听我。但我说这话,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,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”
说完,他收回目光,定定地望着那片吞噬光线的黑暗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仿佛要将那死亡的气息也吸入肺中。然后,他用一种极大的声音呼叫,那声音不像是对洞穴,而是对着死亡本身,对着那一切腐朽与终结的权势:
“拉撒路!出来!”
一片死寂。时间仿佛凝固了。风停了,麻雀不叫了,连哭泣声都哽住了。所有人都屏住呼吸,盯着那个黑洞。心跳声在胸腔里擂鼓。
先是细微的窸窣声,像是麻布摩擦的声音。接着,一个身影,真的,裹着严严实实的细麻布,手脚都缠着布带,脸上也包着布,笨拙地,一步一顿地,从黑暗里挪了出来,站在了刺眼的日光下。
人群爆发出惊骇的尖叫、倒抽冷气的声音,有人跌坐在地上。那不是一个幽灵,那是被束缚着的、实实在在的身体。
耶稣对周围惊呆了的人说,声音平静得仿佛只是解开一个包裹:“解开,叫他走。”
几个胆大的人,手颤抖着,上前去解那些布带。一层层剥开,露出了拉撒路的脸,苍白,带着久不见光的虚弱,但确实是活的,眼睛眨动着,适应着光线。他看着耶稣,嘴唇动了动,没能发出声音,但那双眼睛里,是从最深沉的黑暗归来后,对光明的全然确认。
马利亚第一个扑上去,抱住她的兄弟,号啕大哭,这次的哭声里,再也没有绝望的冰冷,只有灼热的、几乎令人晕眩的狂喜与感激。马大站在一旁,双手捂着脸,肩膀剧烈地抖动,她所有的“信”与“疑”,所有的“务实”与“盼望”,在这活生生的奇迹面前,被冲刷得七零八落,又在一片全新的地基上悄然重建。
耶稣静静地看着这一幕。他脸上没有表演奇迹者的得意,只有一种深沉的、完成使命后的肃穆,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。风吹过,卷起地上的尘土,也带走了坟墓口最后一丝阴郁的气息。他知道,这生命复活的香气,和拉撒路身上残存的死亡气味,将一同飘向耶路撒冷,飘进那些决意要埋葬这一切的掌权者的鼻中。
而在人群之外,那个叫多马的门徒,对同伴低声说了一句日后看来像预言般的话,语气干涩:“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”他那时还不完全明白,这从死里夺回的生命,指向的将是另一座坟墓,和一场为所有人准备的、真正胜过死亡的复活。
黄昏时分,拉撒路坐在自家院子里,身上盖着一条薄毯。他慢慢地喝着一碗马大熬的稀粥,动作还有些僵硬。他不怎么说话,只是偶尔抬起眼,寻找那个坐在不远处的老师的身影,目光相遇时,便有一种无需言语的安然。生命回来了,但某些东西已经永远改变。从那个黑暗里带回来的,不只是呼吸和心跳,还有一种沉默的知晓。
马利亚则拿出一瓶极其珍贵的真哪哒香膏,默默地将膏油抹在耶稣走得起了尘土的脚上。她用头发去擦,动作轻柔而专注。没人责备她浪费,连一向务实的马大也没有。屋子里充满了香膏浓郁的、压过一切的芬芳。这香气,似乎要将下午坟前那最后一丝死亡的气味,彻底覆盖,永远驱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