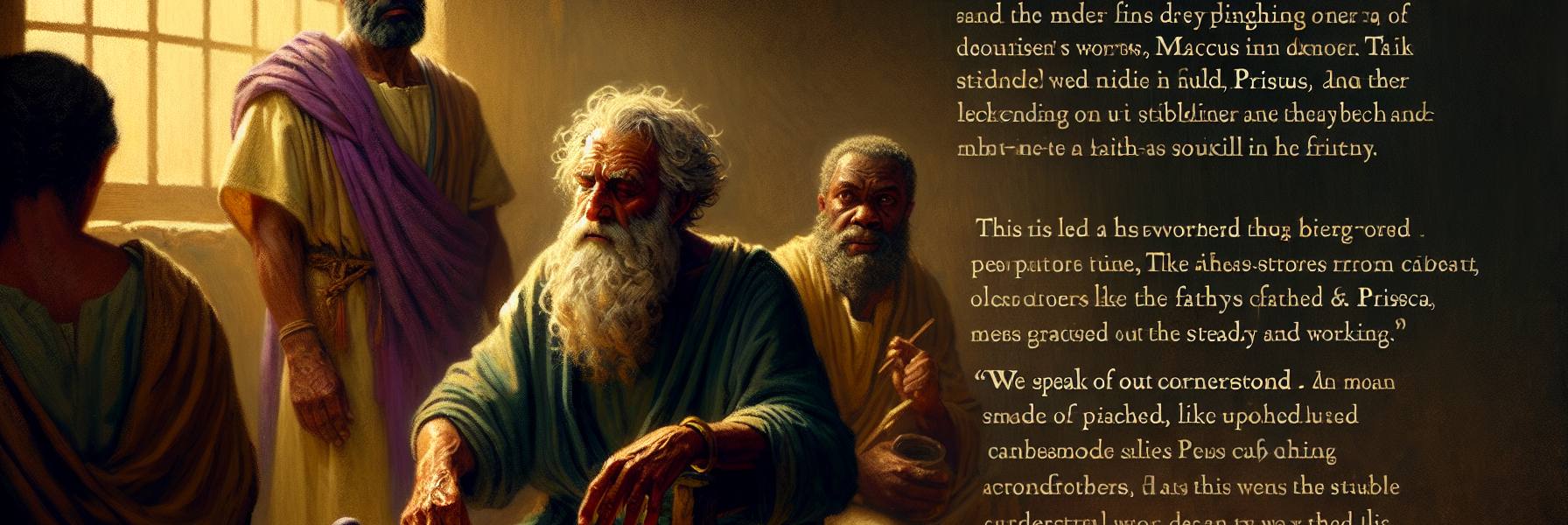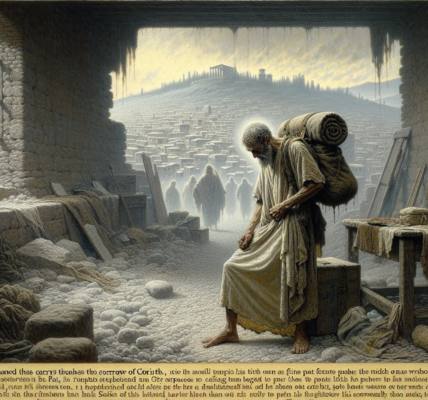石阶被午后的太阳晒得发烫,空气里浮动着橄榄木与陈旧羊皮纸混合的气味。亚基帕坐在廊柱的阴影里,手指拂过面前摊开的经卷,那些黑色墨水写就的字句,在光阴里变得沉静而温润。他是耶路撒冷一个利未支派的抄经士,每日与律法的字句为伴。但近来,他心里总有一片不安的涟漪,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沉寂已久的池水。
这天,一位从罗马来的同乡,名叫马可的弟兄,悄悄带来一卷书信的抄本。信是写给“希伯来人”的,内容新奇而烫人。亚基帕起初只是出于习惯,想看看文士的笔法,却被开篇那恢宏的宣告攫住了:“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、为大祭司的耶稣……”他读到“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,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。” 手指停在“摩西”这个名字上,微微颤了一下。
摩西。对亚基帕而言,这不是一个遥远的名字,而是他每日呼吸的空气。律法是摩西传的,仪式是摩西立的,那引导先祖出埃及、在旷野传达神谕的,是摩西。他的整个生命,他抄写的每一笔划,都筑在这位神人的根基上。如今这书信却说,有一位比摩西更尊荣?
他抬起头,望着圣殿外院熙攘的人群,献祭的烟袅袅上升。他仿佛看见旷野的火柱,听见西奈的雷声。摩西是忠心的,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,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。亚基帕心里承认这一点。但信上说,那位耶稣,却是为设立他的尽忠,如同儿子治理父家。一个念头像微光透进他严谨的思维:仆人与儿子,见证与创立,那预备的与那成全的……这其间的分别,大得令他心慌。
接下来的几日,这些话在他心里发酵。他开始在抄写律法节段时走神,眼前浮现的不再仅仅是字句,而是景象。他看见先祖们在埃及为奴的苦况,看见红海分开的道路,也看见那同样一群人,在旷野的磐石边发怨言,在应许之地的边缘战兢退缩。信上的话像一把钥匙,突然打开了他熟读却未必真懂的往事:“他们四十年的时间,我厌烦那世代……我在怒中起誓说:‘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’”
亚基帕感到一阵凉意。那厌烦,那起誓,对象不是外邦人,正是那蒙了救赎、见过神迹、领了律法的百姓。问题出在哪里?信上的词语尖锐无比:“你们要谨慎,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,把永生神离弃了。” 不信的恶心——不是公然的反叛,而是心底那一点冰冷的疏离,是听见应许时里面的退缩和嘀咕,是不断需要神迹印证却从不满足的顽梗。旷野的漂流行程,原可以短得多。延迟的不是神的应许,是人的心。那“安息”,不只是脚掌踏上的土地,更是一种信靠的状态,是停止自己的挣扎,进入祂成就的工里。
一日黄昏,亚基帕与几位相熟的文士在廊下轻声讨论。一位年长的文士捻着胡须,慢吞吞地说:“这信的意思,似乎说摩西所指的,耶稣所是的;律法所预表的,恩典所实现的。我们若只停在摩西的见证里,却拒绝他所见证的那位,便是辜负了摩西一生的工作,也重蹈了先祖的覆辙。” 另一位年轻些的则忧心忡忡:“可是,这会不会是贬低了律法?” 亚基帕听着,没有插话。他想起信上那劝勉与警戒交织的语调:“总要趁着还有今日,天天彼此相劝,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,心里就刚硬了。”
刚硬。这个词让他想起旷野的磐石,也想起人心里那层日积月累、难以穿透的壳。是习惯了宗教的形式,却对说话的神陌生;是精通律法的条文,却对律法指向的基督漠然。这种刚硬是无声的,它就在每日按部就班的礼仪里,在固守传承却失去焦点的虔诚里。
晚祷的号角吹响了。人群开始涌动。亚基帕卷起面前的经卷和那封书信的抄本,站起身。夕阳将圣殿的石头染成金红色,雄伟而庄严。这一切都是好的,都是神曾经设立的。但信中的话语,像一道更深远的光,照进这壮丽的景象深处。他所站立之处,这殿,这城,这律法的传承,都指向一个更坚固的根基,一位更忠心的“儿子”。而他的“安息”,不在于紧抓这宏伟的影子,而在于信靠那立定影子的实体。
他走下石阶,汇入散去的人群。心里那份长久以来的隐约不安,此刻并未消散,却转化成为一种清醒的紧迫。他知道,有些思索引发的改变,将如暗中的水渗入石缝,缓慢而不可逆转。今日的日光已然倾斜,黑夜将至。但信中的劝勉在他耳中低回,不是严厉的斥责,而是一种带着盼望的呼唤,呼唤人脱离那飘流与刚硬的循环,进入一个更美的、已经预备好的安息。这安息的门,至今仍未关闭。他加快了脚步,身影没入耶路撒冷曲折的街巷,心中反复咀嚼着那个词,那个连结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关键——**“今日”**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