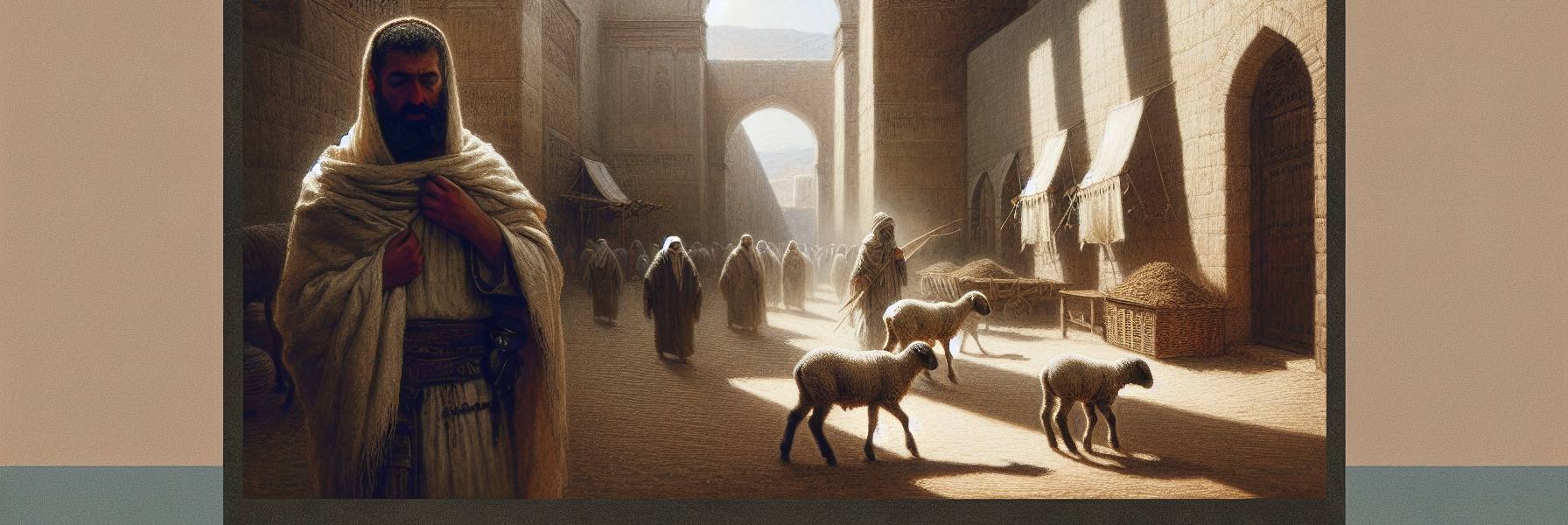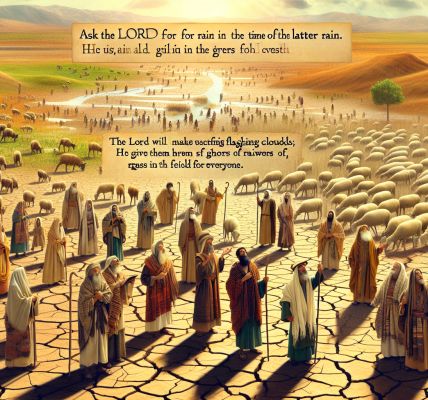烟从燔祭坛的细铜网上袅袅升起,起初是灰白的,混着牲口毛发瞬间焦糊的刺鼻气味,随后渐渐转青,变得纯净,笔直地插入犹大山地午后澄澈的天空。以利亚敬站在坛旁,粗糙的手掌在细麻布衣襟上无意识地搓了搓,仿佛要搓掉那看不见的、粘附在皮肤上的血气和尘埃。
他是个老祭司了,鬓角的白发与胡须一样,被岁月和常年烟火染成一种暗淡的黄色。他见过太多这样的献祭。但今天这个不同。来的是一个年轻农夫,名叫约坍,从山脚下的村庄步行而来,脸上还带着走了长路的红晕与汗迹。他牵来的不是羊羔,而是一头健壮的公牛犊,毛色纯黑,只在额头有一撮星形的白毛。牲口的眼睛大而温驯,湿润的鼻头喷着气,全然不知自己的命运。
“你要献燔祭。”以利亚敬的声音不高,像坛边被风吹动的灰烬,干涩而平静。这不是询问。
约坍点了点头,喉结滚动了一下。他的指节因为紧攥着缰绳而发白。“我……我妻子,生了头胎的儿子。”他开口,声音有些发紧,“平安。母子都平安。我……我心里……”他找不到词,只是抬起眼,望向那黑石砌成的坛,望向那上面永不熄灭的火。火在铜网下低语,吞噬着早晨残留的油脂,噼啪作响。
以利亚敬懂了。不是为特定的罪,不是为玷污。是一种满溢出来的东西,一种沉重而又轻盈的感激,一种在巨大恩典面前感到自身卑微的刺痛。这感觉需要出口,需要一个仪式来盛放,像这燔祭坛盛放火焰一样。他点了点头,示意约坍跟着他走到会幕院子门口。
步骤是古旧而严厉的,由神在西奈山上亲自吩咐摩西,再由摩西教导像以利亚敬这样的祭司。每一步都容不得轻忽,因为每一步都关乎神圣。年轻农夫的手在颤抖,当他按照指示,将手掌沉沉地按在那颗黑色头颅上时。牛犊似乎感到那手掌的重量与热度,不安地动了动蹄子。这一按,是奇特的联合与转移。仿佛约坍整个的生命——他的感恩,他的卑微,他因得子而战栗的喜悦,他身为凡人所有的亏欠——都透过掌心,灌入这头无辜牲畜的生命里。这牛不再仅仅是牛,它成了一个载体,一个代赎的符号。
宰杀的时刻到了。约坍必须自己动手。刀子是铜的,磨得亮,刃口有一道冷冷的青光。以利亚敬站在一旁,看着那年轻人的脸变得比石灰还白,看着他咬紧牙关,手臂却稳得出奇。刀刃准确地划过喉咙,快而深。血猛地喷溅出来,热气腾腾,带着浓烈的生命腥气。约坍没有退缩,他接住血,用祭司递给他的铜盆。血在盆中晃动,浓稠,暗红,映着天光。然后,他端着盆,走到坛的四周,将血洒在那发黑的石基上。血点溅在石头上,嘶嘶作响,很快变成深褐色的斑痕。这是立约的血,是生命归于神的宣告。
接下来的工作,是以利亚敬和他的助手们的事了。两个年轻的利未人上前,利落地将庞大的牛尸剥去皮。皮子被完整地剥下,发出轻微的撕裂声,露出底下鲜红与白色交织的肌肉纹理。那带着白星的黑色毛皮,被卷好放在一旁,它将属于祭司,这是他们的份。以利亚敬接过刀子,开始分解这祭物。他的手极稳,顺着骨骼与关节的缝隙游走,刀刃过处,肌腱分离,骨节脱开。腿、胸、腹、内脏、脂油……被一块块分开,整齐地码放在一旁特制的铜盘里。内脏需要仔细清洗,清澈的水从石缸里舀出,冲去血污和食物的残渣。肠子在水中呈现出一种滑润的淡粉色。
院子里只有水声、刀刃与骨头偶尔相触的轻响,以及火焰持续的吞吐声。没有人说话。肃穆包裹着他们,像一件看不见的祭服。约坍站在一旁,看着自己的感恩——那活生生的、呼吸过的、走过长路的牛——被分解,被处理,变得有序,预备归于那火。他脸上的红潮褪去了,只剩下一种深沉的、近乎疲惫的平静。那满溢的情感,仿佛随着血洒出,随着这有条不紊的分解,被导入了正当的河道。
最后,所有的肉块,连头带腿,还有洗净的内脏,都被搬到坛前。铜网上的火,因为即将到来的盛宴而欢腾起来,窜得更高了些。以利亚敬亲手将这一切,一样一样,安放在火上。先是铺上脂油,那是最好的部分,火舌立刻贪婪地舔舐上去,爆出更明亮的光芒和滋滋的声响。然后是大块的肉,沉重的腿肉,丰厚的胸肉。火接纳了它们,包裹了它们。火焰的颜色变幻着,从橙红到金黄,边缘带着透明的蓝。浓烟再次升起,但这次不同,烟雾里弥漫开一种奇异的香气——不是焚烧垃圾的臭味,而是肉食烧熟、油脂燃烧时特有的,一种丰腴的、近乎抚慰的气味。这香气,就是献与耶和华“馨香的火祭”。
以利亚敬退后一步,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。烟熏得他眼睛有些发涩。他看着那火,看着那在火焰中逐渐消失的祭物全部。燔祭,全然的祭。不保留一分一毫,完全献上,完全焚烧,完全化为烟云,升到至高者面前。这头牛,连同约坍按手时倾注的一切,不再存在于地上了。它成了烟,成了香气,成了属天范畴里的东西。
约坍还站着,望着那团吞噬一切的火。他的肩膀松弛了下来,好像卸下了一副看不见的重担。火光在他年轻的脸上跳动,那里面有什么东西被洁净了,也被坚固了。他没有说话,只是深深地向着祭坛,也向着老祭司,鞠了一躬,然后转身,沿着来路下山去了。他的身影越来越小,最后消失在山路的拐角。
以利亚敬又站了一会儿,直到坛上的火焰渐渐恢复平稳的燃烧,只剩下一些通红的炭和白色的灰。夕阳西下,将坛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助手们开始清理场地,用灰铲收取灰烬,拿到营外洁净的地方倒掉。
起风了,从东边的旷野吹来,带着干燥沙石的气味。但风过之处,那燔祭的香气似乎仍未散尽,一丝一丝,萦绕在院子的角落,萦绕在老人的记忆里。他转身,慢慢走向自己的帐篷,脚步踏在夯实的土地上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这就是日常,这就是神圣与凡俗交界处的、带着血与火气味的日常。而这,就是道路。人带着他一切沉重或欢欣的“所有”,来到这火面前,看着它被全然接纳,又全然消失。回去时,身上便染了那火的温度,和那烟的痕迹。虽然明日,生活的尘埃会再次落下,但这片刻的“全然”,已足够支撑他,继续走那漫长的、回家的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