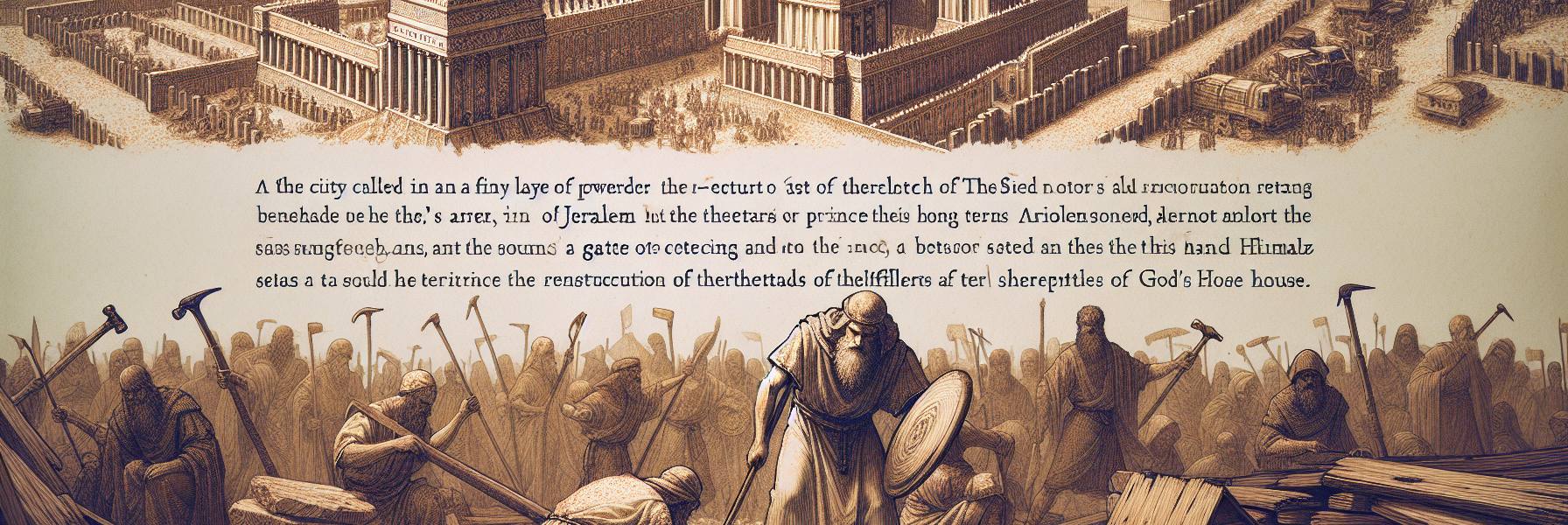晨雾还贴着橄榄山的脊背,耶路撒冷的石头却已开始吸收第一缕温热。那热,像昨日剩下的,又像从地底深处新冒上来的。玛基雅推开木门,门轴发出一种漫长而沉钝的呻吟,仿佛它记得比人更久远的事——被掳前的油脂,被焚时的烟尘,以及如今归回后的、带着生涩希望的每一次转动。
他是可拉家族的后裔,一个守门的人。
名单是冗长的,羊皮卷上名字挨着名字,像葡萄串上挤挤挨挨的果实。但人不是名字。人是有气味、有重量、有各自磨损痕迹的。比如俄别以东,他的指节粗大,是常年托举圣殿门闩的结果;比如示利米雅,他的耳廓似乎比别人薄些,因为他总在寂静的深夜里,最先听见远处巡更的梆子响。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,回到这座尚未完全褪去焦痕的城,回到这份祖辈相传的、看守神殿门户的职分上。职分不是荣耀,是每日肩头真实的压力,像汲水的陶罐压在女子头顶,需要一种平衡的、沉默的技艺。
玛基雅沿着外墙慢慢走。他的手拂过石面,有些地方还留着烟熏火燎的黑色指甲盖大小的斑痕。他的父亲,父亲的父亲,都未曾见过所罗门圣殿的辉煌。他们口传的,是那些金灯台、香柏木板的荣光,但更真切的记忆,是石头倾塌的巨响,是浓烟蔽日的恐慌,是异乡河畔,柳树上挂不牢的、喑哑的琴。如今他们回来了,圣殿远未复旧观,但他们看守的这片土,这片立着粗糙祭坛、回荡着试探性颂歌的土,就是全部的意义了。看守,意味着你必须第一个醒来,最后一个睡去;意味着你的眼睛要分辨朝圣者脸上的虔诚与匆促,你的耳朵要过滤风声、鸟声与可能潜近的窸窣异响。
他转到东门,这里正对着初升的日头。光是一点一点爬过来的,先染亮最高的那块堞垛,再漫过墙脊,最后哗啦一声,铺满了整个内院。晨祭的时候到了。他能看见亚玛帅家族的祭司们,穿着浆洗得有些僵硬的细麻布衣,端着铜盆,步履谨慎地走向祭坛。他们的神态是收敛的,甚至有些过于严肃,仿佛每一次呼吸都在掂量是否合宜。被掳归回后的祭司职分,少了些天然的王家气派,多了些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的敬畏。族谱被反复核查,世系必须清清楚楚,一点不容含糊。因为血统的纯正,成了连接那个断裂时代最脆弱的丝线。
玛基雅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。比如耶何耶大,一个沉默的青年,手却极稳,处理祭物时有一种近乎哀戚的专注。还有米拉利族的利未人,他们在殿里管理器物,数目要日日点算:盘子、刀子、金盂、银匙。他们交接时,眼神的交接比物品的交接更郑重,仿佛移交的不是物件,是一份托付,一份从摩西时代传下来的、关于“圣”的脆弱概念。一个豁口的碗或许还能盛水,但若它是圣所的碗,那豁口便成了一个需要全体会众禁食祷告的事件。
白日漫长。有便雅悯人从基遍、密抹来,带着田间的土产和满脸的风霜;有犹大人从希伯仑的山地下来,袍角还沾着荆棘的刺。他们来献祭,来还愿,或仅仅来看一眼。玛基雅和同伴们要辨认,要引导,有时也要温和地拦阻。一个眼眶通红的老妇想冲入内院,她手里攥着一只瘦小的斑鸠,喃喃说着儿子在巴比伦患的热病。他们扶住她,听她语无伦次的话,引她去见当值的祭司。规矩是冷的,但执行规矩的手,可以带着体温。
黄昏来得很快,像一件深蓝色的袍子,从汲沦溪谷那边缓缓抖开,罩住了城。灯要点起来了。圣所里的灯,与寻常人家的灯不同,那光是任务,是象征,是不能间断的守望。玛基雅交卸了白日的职事,但没有立刻回家。他喜欢坐在一段残损的矮墙上,看星光一粒一粒钉上夜幕。城里有炊烟升起,有母亲呼唤孩童的声响,有铁匠铺最后一声捶打后的寂静。这些声音,这些景象,就是他们从远方回来的目的——不是为了重建一座无与伦比的宫殿,而是为了让炊烟能在约定的祭坛旁升起,让孩童的啼哭能在应许之地的夜空中飘荡。
他想起了族谱上那些名字,那些他曾觉得枯燥的“某某生某某”。此刻他忽然觉得,那些名字不再是羊皮上静止的墨迹。他们是活过的。有喜乐,有恐惧,有顺服,有悖逆,有在巴比伦的炉火边固执地持守安息日,也有在归途的旷野里因疲惫而生出的怨言。而这一切,像一道蜿蜒却未曾彻底断绝的溪流,流过了燃烧的城、流过了异国的河,最终流到了这片仍在重建、仍有伤疤的山丘上。
他的名字,玛基雅,也会在那卷子上。不是作为君王,不是作为先知,只是作为一个“守门的人”。他知道,明日清晨,门轴依旧会发出那声沉钝的呻吟。他会推开它,让第一缕光,照进圣所的院子。而那份长长的名单,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开门、关门声中,在祭司缄默的步履中,在利未人清点器物的低语中,获得了一种比石头更沉的重量,和比晨雾更真实的形态。
夜凉了。他跳下矮墙,拍了拍手上的灰。回家的路很短,黑暗中,他脚下的石头路,却仿佛连接着一条极其漫长、从亘古延伸到如今的路。路上行走的,是一个个有名字、有气息、有弱点的普通人。他们的故事,就是圣殿的故事;他们的守望,就是约的守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