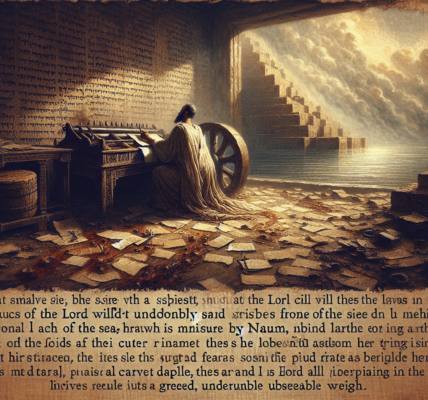窑匠的巷子在耶路撒冷的下坡处,靠近粪厂门。那股味儿,你得先习惯——泥土的腥气,混着柴烟、水汽,还有旁边羊市飘来的牲畜粪便与干草的气息,热烘烘地纠缠在一起,钻进你的鼻孔,粘在你的衣服上。我常去那里。不是去买陶器,而是去看那窑匠。
他年纪很大了,背佝偻得像一把拉满了却松了弦的弓。两只手出奇地大,指节嶙峋,布满深深浅浅的割痕与烫疤,像老树的根。他很少说话,全部的言语似乎都给了那转动的轮子和手里的泥。他的作坊很暗,只有门口和屋顶缝隙透进几束光,光里浮动着无数微尘,像是静止的,又随着他的动作缓缓旋舞。那是个闷热的午后,我蹲在门槛外的阴影里,看着他工作。
轮子转动的声音单调而持续,吱呀——吱呀——,像一种古老的叹息。他脚踝有节奏地蹬着,那圆盘便平稳地旋转起来。他从水桶旁挖起一大团湿泥,“啪”地一声摔在轮盘中央,那声音饱满而结实。泥是上好的泥,来自汲沦溪边的坑,澄得细腻,柔韧。他的手先拢住泥团,随着轮转,泥团慢慢升高,变成一个粗矮的圆柱。水光在泥上滑动。
然后,神奇的事发生了。他粗糙的拇指稳稳地摁进泥柱的顶端,缓缓下压,同时另一只手从外侧轻轻拢住。那混沌的一团,开始有了形状,有了意图。泥土在他手里仿佛有了生命,顺服地随着他指尖的力道向外舒展,向上生长。我看见一个陶罐的雏形——底部宽而稳,腹部渐渐鼓胀,那是预备盛装酒或油的地方。他的手极其稳定,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温柔。水多了,就用干布抹去;形状歪了,便稍稍加力扶正。泥土在他的引导下,正成为一件有用的器皿。
就在那时,轮子似乎被一粒坚硬的石子硌了一下,或许泥里本就藏着杂质。那已具优美弧线的陶罐腹部,突然不受控制地扭曲,一块泥凸了出来,整个结构开始晃动,变得一边厚,一边薄,摇摇欲坠,眼看就要瘫软下去。
窑匠没有惊呼,甚至没有皱眉。他只是停下了脚。轮子慢下来,吱呀声变得绵长,终于静止。他盯着那团失败的泥,看了片刻,眼神里没有怒气,只有专注的审视。然后,他伸出那双大手,毫不犹豫地将那已成形的、却有了瑕疵的陶罐,一把拢住,压塌,重新揉成了一团混沌的湿泥。
他将那团泥捧起,在手里掂了掂,又“啪”地一声摔回轮盘中央。再次用脚启动轮子,吱呀——吱呀——。从头开始。水,手势,压力,引导。这一次,泥似乎更顺从了。他没有试图再做同样的陶罐。在他的手中,那团泥渐渐变成了一个形状不同的器皿——一个矮胖的、敦实的坛子,口沿厚实,看起来能装更多谷物,更耐磕碰。似乎这,才是这团泥本应成为的样子。
我坐在那里,浑身僵硬,仿佛被那景象攫住了呼吸。喧闹的市声——羊叫、人语、远处的驼铃——忽然退得很远,很远。只剩下眼前这沉默的老人,这转动的轮,这团被重塑的泥。窑匠的手,泥的命运。
一个声音,不是耳朵听见的,却比窑匠拍打泥坯的声音更清晰地,在我里面响起:
“耶利米,你看见窑匠所作的么?”
我张了张嘴,发不出声音,只在心里点头。
那声音继续说,如同深远处的雷,滚过我的肺腑:“以色列家啊,我不能待你们如这窑匠待泥么?看哪,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,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。”
我猛地闭上眼,热泪却冲破眼皮,混着脸上的尘土,流下沟壑。我看见的不是这幽暗作坊的景象了。我看见北方阴沉的天空下,亚述人战车扬起的尘土;我看见南边荒漠灼热的风中,埃及法老闪亮的金冠。我看见犹大的群山,耶路撒冷的城墙,圣殿的金顶在日光下闪耀——然而那光,在我看来,却像即将冷却的灰烬最后的余光。我看见百姓的面孔,在市集上为蝇头小利争吵,在邱坛上向不能救人的木头石头屈身,在暗处行那些可憎的事,脸上却带着诡诈的平安。他们就像那团泥,里面混进了坚硬的石子,是骄傲,是贪婪,是流无辜人的血,是背弃了古老的约。他们正歪斜,正扭曲,正变成一件危险的、无用的器皿,随时会崩塌成一滩烂泥。
“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,说要拔出、拆毁、毁坏,倘若那国转意离开他们的恶,我就必后悔,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。”
声音里有严厉,却也有缝隙,那缝隙里透出的,是何等令人心碎的盼望!就像窑匠审视那瑕疵的陶罐时,眼中不是毁灭的光,而是重新创造的可能。悔改。回转。这是唯一的活路。是那团泥被重新塑造的机会。
“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,说要建立、栽植,倘若他们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,不听从我的话,我就必后悔,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。”
福气。栽植。建立。这些词曾像甘霖落在我们先祖干旱的梦里。但若那被栽植的树,自己把根从活水旁拔起,执意伸向毒沼呢?若那被建立的城,自己拆毁根基的石头,去建造巴力的柱像呢?那赐福的手,也能收回;那建立的力量,也能倾覆。窑匠的手,既能塑造,也能毁坏那不合格的,再重新开始。
景象消散了。我睁开眼,窑匠正用一根细绳,将他新做好的坛子从轮盘上割离。他双手捧起它,像捧着一个新生的婴孩,将它轻轻放在木架上,与其他等待晾干的器皿排在一起。那坛子沉默地立着,粗朴,却完整,等待着入窑经受烈火的试炼。
我踉跄站起身,腿脚有些麻木。巷子里的气味再次将我包围。我转身,慢慢地走上坡,向城里去。脚步沉重,心里却烧着一团火,那火里混合着极大的悲痛和一份极其清晰的托付。我要去对他们说,对这座自以为坚不可摧的城,对这些自以为是被特别挑选、绝不会被舍弃的百姓,说出这窑匠与泥的比喻。
我知道他们会怎么回应。他们会笑,会怒,会说:“这是耶利米,总是说凶言的人。”他们会像那含有杂质的硬泥,抗拒窑匠的手。结局,我已从静止的轮盘和那被重新揉捏的泥团中看见了。
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,斜斜地印在耶路撒冷斑驳的城墙上,像一道深深的裂痕。圣殿的轮廓在天际显得黑沉。我心里响起最后的、低语般的话语,那是给我,或许也是给所有能听见之人的:
“看哪,他们却说:‘这是枉然!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,各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作事。’”
风从东边的旷野吹来,带着干燥的死亡气息。我紧了紧衣袍,继续向前走。手中虽空无一物,却仿佛已捧着一团亟待成形、却也极易破碎的泥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