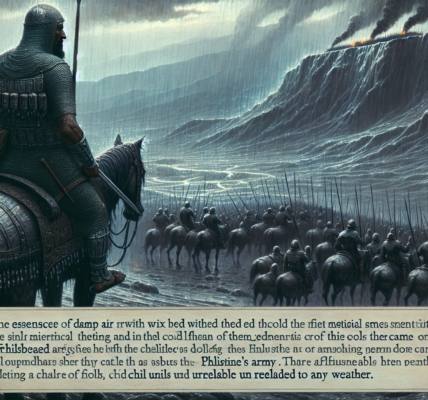橄榄山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像墨迹在逐渐冷却的石头上洇开。耶路撒冷在脚下喘息,白日尘埃落定,空气中浮着节日前夕那种焦躁的甜味,混杂着未熄的炊烟与远处圣殿飘来的淡淡燔祭气息。
西门家里比平日拥挤。人们低声说话,手脚放得轻,目光却不时瞥向同一个方向——祂坐在靠里的位置,脸上有种深沉的平静,像风暴中心的无风带。马利亚进来时,几乎没人注意她。她手里捧着的玉瓶是雪花石膏的,在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,像捧着一截凝住的月光。她跪下,没有说话,只是拧开瓶盖。刹那间,一股尖锐的香气劈开室内的沉闷,是极纯的哪哒香膏,浓郁得几乎可以触摸。她将膏倾倒在祂的头上,清亮的油液顺着发丝流淌,滴落在肩头的粗布衣袍上,迅速洇开深色的圆斑。那香气太霸道了,充满了整个屋子,钻进每个人的鼻孔,甚至盖过了桌上无酵饼的味道。
“何必这样枉费呢?”声音从门边响起,带着刻意压低的、却足够让所有人听见的不满。是犹大。他手指无意识地搓捻着衣角,那是他盘算时的习惯。“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,周济穷人。”他的话引来几声含糊的附和,像是投入静水的小石子。
祂转过头,目光越过众人,落在马利亚仍微微颤抖的肩上。“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?”祂的声音不高,却让所有私语戛然而止。“她在我身上作的,是一件美事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,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”顿了顿,那话里忽然浸透了某种沉重的东西,像浸透了水的羊毛:“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,是为我安葬作的。”
“安葬”这个词像一块冰,滑进温暖的房间。无人接话。连犹大也抿紧了嘴唇,眼神却飘开,落在地上某块摇曳的光斑上。马利亚用头发轻轻擦去滴落在祂脚背的膏油,极轻的啜泣声,被宏大的香气吞没了。
黄昏最后的光彻底死去。黑暗从窗棂外漫进来,与室内的昏黄纠缠。祂吩咐门徒预备逾越节的筵席。楼上房间已经备好,宽敞,铺着洁净的席子,中央长桌上摆着羔羊、苦菜、泥状的果仁酱。羊脂蜡烛的光,把十几个晃动的影子投在墙壁上,巨大而模糊。
他们坐定。咀嚼声,陶器轻碰声,夜风吹动布幔的窸窣声。就在这寻常的节期氛围里,祂的声音再次响起,斩断了平静:“我实在告诉你们,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”
这句话像一根针,刺穿了筵席的皮囊。空气骤然收紧。门徒们停下一切动作,愕然相顾,每张脸上都写满惊疑与受伤。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问:“主,是我吗?”声音里有战兢,有不解,有急于辩白的痛切。
犹大也问,或许问得最晚,声音混在其他人尾音里,平稳得听不出波纹:“拉比,是我吗?”他手里捏着一块饼,指尖用力到发白。
祂蘸了一点酱,递给他。“你说的是。”声音很轻,仿佛一声叹息。那蘸了酱的饼,在递出的瞬间,成了一个隐秘而可怕的记号。犹大接过去,很快地放进嘴里,咀嚼,吞咽,动作流畅。然后他站起来,说有点事,便转身没入楼梯的阴影里。没人拦他,或许大家都以为他是去处理周济的事,或是为节期作什么安排。门在楼下轻轻合上,一声闷响。
他走后,房间似乎宽敞了些,却又更加空洞。祂拿起饼,祝谢了,擘开。“你们拿着吃,这是我的身体。”又举起杯,祝谢了,递给他们。“这是我立约的血,为多人流出来,使罪得赦。”话语简单,分量却重得让举杯的手发沉。葡萄汁在陶杯里漾着暗红的光,像某种深不可测的预示。
饭后,他们唱了一首诗篇,是逾越节必唱的哈利路诗篇。歌声不算齐整,有些沙哑,在空旷的夜里传不远,便消散在橄榄树丛间。他们出了城,穿过汲沦溪。溪水在月光下是一道蜿蜒的银箔,水声潺潺,衬得夜更静。进了客西马尼园,熟悉的油橄榄树张开虬结的枝干,树影婆娑,在地上印出破碎的图案。祂带着彼得、雅各和约翰往深处走了一小段,脚步越来越慢,终于停下。祂的脸在月光下显得灰白。
“我心里甚是忧伤,几乎要死。”这话从祂口中说出,带着一种陌生的、近乎软弱的颤音。祂吩咐他们:“你们在这里等候,和我一同警醒。”便又往前走了约扔一块石头的距离,俯伏在地。那三个门徒靠在老树干上,疲倦如潮水般涌来。他们听见祂祷告的声音断断续续,被风吹过来,听不真切,只捕捉到“我父啊”、“这杯”、“不要照我的意思”几个零碎的词。夜越来越深,寒意沁入布衣。他们的眼皮沉重地合上,又勉强睁开,如此反复。忧伤太沉重,而肉体太疲乏。
不知过了多久,祂走回来,脚步踩在落叶上的声音惊醒了他们。祂看着他们,那眼神里没有责备,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哀怜。“怎么样?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?”祂说,“总要警醒祷告,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,肉体却软弱了。”
如此三次。祂去祷告,回来,看见他们沉睡。第三次回来时,祂没有再叫醒他们。因为脚步声已从园子入口杂乱地传来,火把的光撕裂了林间的黑暗,晃动的人影幢幢,夹杂着金属摩擦的轻响与压低的呼喝。
他们来了。许多人,带着刀棒,是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来的。走在前面的,是犹大。他径直走到祂面前,叫了一声“拉比”,然后上前亲吻祂。那是一个绵长而用力的吻,印在脸颊上。火把的光照在犹大脸上,他闭着眼,仿佛不忍看,又仿佛已置身事外。
“朋友,你来要作的事,就作吧。”祂说。这句话像是对整个夜晚、对所有预兆、对那蘸酱之饼与三十块银钱的一个最终确认。
人们一拥而上。彼得拔出刀,挥砍,削掉了大祭司仆人马勒古的一只耳朵。喝斥声,惊叫声,火把乱晃。“收刀入鞘吧!”祂的声音压过混乱,“凡动刀的,必死在刀下。”祂甚至伸手摸了摸那仆人的耳朵,血就止住了。然后祂转向那些捉拿祂的人,语气里有一种奇特的威严:“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,如同拿强盗吗?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,你们并没有拿我。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,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。”
那一刻,门徒都退后,四散,逃入橄榄树更深的黑暗里,连彼得也不例外,他的脚步踉跄,粗重的喘息声很快被夜色吞没。
他们把祂带往大祭司该亚法的院里。夜已深,但院里燃着炭火,仆役和差役围着取暖,火光映着一张张好奇而冷漠的脸。彼得远远跟着,直到院子外面。他混在杂役中间,也凑到火边,搓着手,假装只是为了取暖。
里面传来隐约的呵问声,拍案声。外面,一个使女借着火光仔细看了看彼得,忽然说:“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。”
彼得心里一紧,避开众人的目光:“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”他退到门口阴影处。但另一个使女更肯定地对旁边的人说:“这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。”彼得发誓起誓:“我不认得那个人!”
过了不多时,旁边站着的人围过来,其中一个是大祭司的仆人,被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,他盯着彼得:“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?”
彼得这次是发咒起誓:“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!”话音未落,鸡就叫了。第二遍。
就在鸡啼穿透清冷晨雾的瞬间,里面的声音似乎静了一静。主转过身来,隔着庭院,隔着晃动的人影与跳跃的火光,望了彼得一眼。只是平静的一眼。彼得却像被那目光烫到,猛然记起不久之前,就在这夜色未浓时,在楼上房间里说过的话:“今夜鸡叫以先,你要三次不认我。”他冲出院子,浓重的黑暗包裹了他,他再也忍不住,失声痛哭。那哭声压抑而破碎,消失在耶路撒冷迷宫般曲折的街巷石墙间,无人听见。
东方,天空透出第一缕鱼肚白,冰冷地抹在山脊线上。夜快要尽了,而最深的黑暗,似乎才刚刚开始。园子里,哪哒香膏那挥之不去的香气,早已被风吹散,只留下泥土、落叶,和即将到来的白昼那干燥而残酷的气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