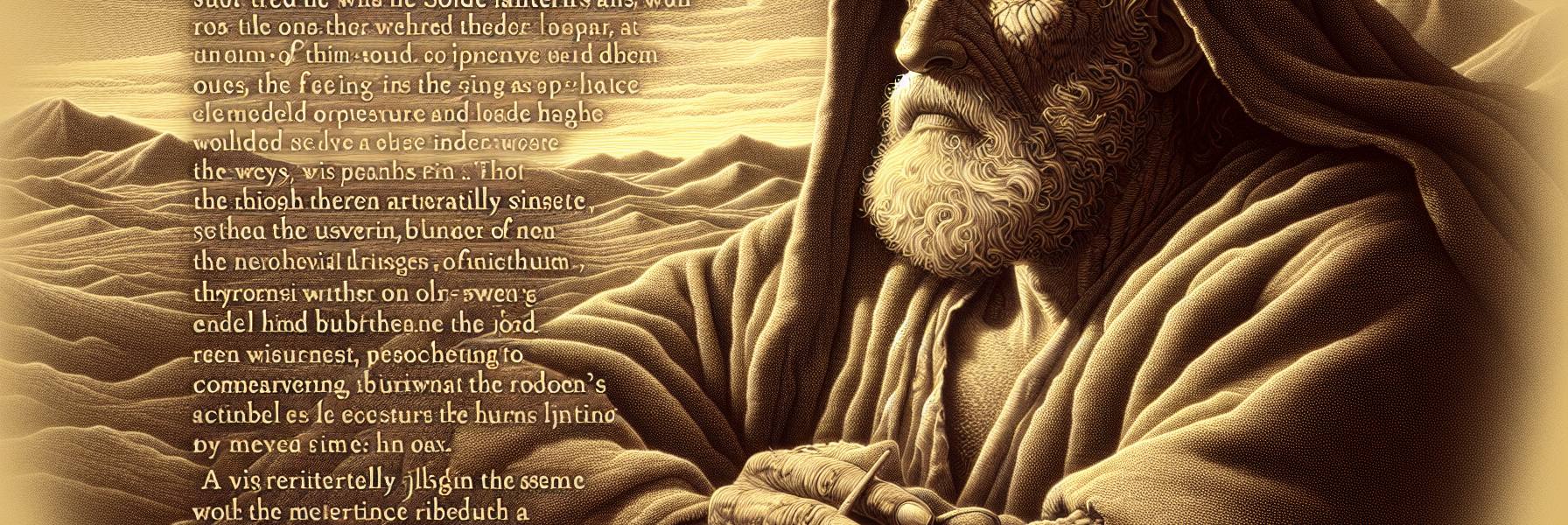(一)
那時,我走出帳棚,腳下的泥土還帶著夜露的濕潤。東方剛泛起魚肚白,山脊的輪廓像沉睡巨獸的背脊。風從曠野那頭吹來,帶著枯草與塵土的味道,卻也帶著回憶的重量——那幾乎可以觸摸的重量。
我曾有過那樣的日子。
光,是的,那時我的日子裡滿是光。不是這種懸在頭頂、刺得人睜不開眼的烈日,而是一種從內裡透出來的溫潤光澤,像秋日午後的蜜,流淌在每一個平凡的日子裡。上帝待我的情誼,好像總是比旁人多一些。祂的燈,曾經那麼穩定地照在我的額上,以至於我走過最深的幽谷,也不覺得腳下有黑暗。
我的路,是用奶與油鋪成的。不是比喻。羊群多得像移動的雲,壓低了山腰的草場;橄欖樹的果子多得壓彎了枝,擠出的油,金燦燦地裝滿了石鑿的池子。田地也順服,一鐮刀下去,麥穗沉沉地垂著,幾乎叫收割的人直不起腰。但那不是最要緊的。最要緊的是,我知道這一切從何而來。我清晨獻祭,黃昏也獻祭,煙氣裊裊上升的時候,心裡是滿的。那不是驕傲,是一種孩子承蒙父愛的妥帖。
(二)
城門口的老無花果樹,枝葉蓊鬱如華蓋。那是我坐堂斷事的地方。他們會把難處帶到我面前——兩家為了一口井爭執,寡婦被強橫的鄰舍欺壓,外鄉人迷了路又失了驢。我坐在那磐石磨光的座位上,少年人見了我,會悄悄退到一旁,連白髮的長老也起身站立。他們等我說話。
我不是憑著聰明說話。我是先靜靜地聽,聽那憤怒裡的委屈,聽那指控底下的恐懼。等風暴在他們胸中稍歇,我才開口。話語有時像雨,滋潤乾裂的心田;有時像鑿子,剝開層層偽裝,直抵核心的公義。我為瞎子的眼,為瘸子的腳。我打碎不義之人的牙,從他齒縫中奪回被搶奪的。那時我常想:我若見有人因無衣死亡,或見貧窮人毫無鋪蓋,我這肩豈不從頸上脫落,我這臂豈不從肋骨處折斷?
他們信我。不是怕我,是信我。我一笑,他們臉上緊繃的紋路便鬆開了;我點頭,他們就知道事情有了指望。我像首領出行,眾人環繞;又像軍兵元帥,安營時民心安定。我的言語如雨滴落在焦土上,他們張口承接,如同久旱逢甘霖。
(三)
還有那些更細微的時刻。
市場的喧嚷裡,賣陶器的小販會突然停下叫賣,朝我點點頭。汲水的婦人把水罐暫放在道旁,輕聲說:「願你平安,約伯。」連孩童玩耍,見我經過,也會暫時停下,用清亮的眼睛望著,然後被母親輕輕拉回身邊,低聲教導:「瞧,那是個義人。」
他們說我穿上公義為衣,公平如外袍和冠冕。這話太重,我不敢當。我只知道,看見孤兒的眼裡有了光,聽見寡婦夜裡不再哭泣,我的心就像新酒在皮袋裡發脹,滿滿的,快要溢出來。那是一種比銀子更沉、比金子更亮的滿足。
曠野的涼風把我從回憶里拉回。眼前是焦土,是破碎的瓦礫,是三個沉默而坐的朋友。我的皮膚緊繃、發黑,像火爐裡撈出的炭。那「磐石般的時光」,碎了,碎得像摔在地上的陶罐,再也拼不回原樣。
光,什麼時候熄滅的呢?我不知道。燈盞被打翻時,油是先慢慢流盡,然後燈芯才「滋」地一聲,沒入最後一縷青煙。我的青煙,大約也散在曠野的風裡了。
我閉上眼。不是為了不看現今的荒蕪,是為了再看一眼——哪怕只是一眼——那些被神諭般的慈愛所包裹的日子。它們是真的,比此刻我骨頭裡的疼痛更真。
風繼續吹著,帶著無盡的沙粒,擦過我的臉,像時間粗糙的手。
(那時,誰像我呢?誰像如今的我呢?這問題懸在乾熱的空氣裡,沒有迴音。只有曠野,無邊無際地伸展,吞下了所有的答案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