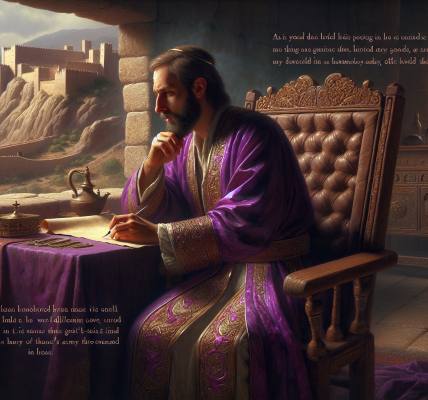夕阳将耶路撒冷的城墙染成一种沉重的赭红色,仿佛一块冷却的烙铁。俄备得裹紧身上的羊毛外衣,立在锡安山的高处,目光却越过层叠的屋宇,投向北方隐约的山影。风从那个方向吹来,带着旷野的尘土气息,也带来一种无声的、却压得人胸口发紧的喧嚣——那不是声音,而是一种气息,一种众多营盘聚集、刀剑磨砺、人心被同一个险恶意念烧灼所散发出的气息。
他知道那是什么。消息像惊鸟一样早已飞遍犹大全地:以东人、以实玛利人、摩押人、夏甲人、迦巴勒人、亚扪人、亚玛力人、非利士,还有那推罗的居民……他们聚集了。不是零星的劫掠,不是边境的摩擦,像一张精心编织的网,从东南西北缓缓收拢。他们商议,彼此结盟,签下密约。俄备得仿佛能听见那些帐篷里压低的、兴奋的耳语:“来吧,我们将以色列的草地从地图上抹去,使这名不再被记念。”
这句话在他心里激起一阵冰冷的战栗。不是为他自己这具已近老迈的躯壳,而是为那名——耶和华的名。他们真正想铲除的,岂止是这些石头城墙,这些葡萄园与羊群?他们是要将那立在锡安、曾在红海分水、在西奈颁布律法、引领先祖的名,一同丢进遗忘的深渊,仿佛祂从未存在过。这种狂妄,比刀剑更让俄备得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。
他走下城墙的台阶,脚步在石板上发出空洞的回响。城内的气氛像绷紧的弓弦。妇女们聚在水井边,交谈声短促而焦虑;孩童似乎也察觉到不安,少了往日的嬉闹。空气中弥漫着烘烤无花果饼的微甜与炭火味,但这日常的温暖,此刻却显得脆弱不堪。俄备得回到自己简陋的居所,墙角的陶灯已经点上,光影在粗糙的墙壁上摇晃。他跪下来,脸伏在冰冷的地上。话语,不是他自己的话语,像是从记忆的深处,从民族的血脉里涌上来,挤迫着他的喉咙。
“神啊,求你不要静默;神啊,求你不要闭口,也不要不作声。” 他低声说,声音干涩。静默,有时比仇敌的呐喊更可怕。那是仿佛被离弃的旷野,是祷告仿佛撞上天花板又弹回的窒息感。他祈求那静默被打破。
然后,像展开一幅血腥的画卷,他眼前浮现出那些同盟者的面孔,不是具体的容貌,而是他们背后所代表的那股吞噬一切的敌意。以东,那以智慧闻名却充满兄弟相残之恨的后裔;以实玛利,那旷野中如野驴般不受羁绊的力量;摩押与亚扪,从乱伦而生,始终带着阴险的妒恨环伺在侧;非利士,海岸平原上傲慢的定居者,歌利亚的子孙;还有推罗,那倚靠财富与海运自比为神的城邦……他们如今竟像合伙的盗贼,分了赃物,便击掌盟誓,要一同来瓜分雅各的产业,要得这“青翠之地”为业。
俄备得的祷告变得急切,如同困兽的喘息。“我的神啊,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,像风前的碎秸。” 他渴求一种彻底的、彰显公义的毁灭。不是人的刀剑能完成的,那太局促,太容易被归功于偶然或战术。他求的是自然界最狂暴、最无可抵御的力量——烈火吞噬森林,狂风席卷山岭,大能者的暴风惊吓他们。不是因为残忍,而是为了让那张狂的、欲将神的名踏在脚下的脸面,布满羞愧与惊惶,直到永远。
这时,一个更深、更远的记忆,穿透眼前的危机,照亮了他内心的黑暗。他的思绪飘向了更古老的年代,飘向基顺河边那片狭窄的平原。他仿佛看见了西西拉庞大的铁车队伍,在突如其来的豪雨中陷入泥泞,动弹不得。他看见了底波拉与巴拉率领的微弱以色列民,如同从高处冲下的山洪。那不是人的得胜,那是神的指头在划动。还有米甸人,像蝗虫一样多, Gideon(基甸)那区区三百人,靠着角、火把与呼喊,便使庞大的营盘在自相残杀中崩溃。那是神用最微小的器皿,彰显最大的嘲讽。
“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,” 俄备得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,“如待西西拉,如待在基顺河的耶宾。” 这些名字,是刻在民族记忆里的碑文,是神作为的见证。他们也曾如此联盟,如此强横,最终却如粪土朽烂在田地里,他们的名号只沦为后世提及神审判时的一个注脚。
祷告到了最后,不再仅仅是关乎眼前的拯救。一种更辽阔、更灼热的渴望,从他心底燃烧起来。这渴望超越了个人与民族的生死存亡,触及了神心意的最深处。“使他们知道:惟独你名为耶和华的,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!”
这才是终点。让那些密谋的、嗤笑的、高举自己名号的邦国,在无可推诿的失败与审判中,被迫承认——不是出于礼仪,而是出于绝望中的认知——他们所要抹去的那个名,是宇宙间唯一真实、至高无上的权柄。让他们在惊惧中,寻见那唯一的真理。这认知,或许比毁灭本身,更是一种终极的、带着怜悯的胜利。
俄备得抬起脸,陶灯的光映亮了他眼中未干的湿痕与深处的一点微火。城外的风似乎更紧了,呜咽着掠过屋檐。危险并未解除,那迫近的营火或许明天就会映红天际。但他胸腔里那块冰冷的铁,仿佛被那更古之火的记忆熨烫过,不再只是僵硬地沉坠。他缓缓站起身,腿脚有些麻木。他推开木门,再次走上夜色笼罩的城墙。远方,敌营的方位,只有一片深沉的黑暗,与天上沉默的星河。
他静静地站着,成了一个剪影。他的祷告,如同一声叹息,融进了耶路撒冷的夜风里,飘向那垂听者耳中。他知道,胜负不在于城墙的厚薄,兵卒的多寡,而在于那名是否仍然看顾这地。而历史,那部由神亲自书写的长卷,曾翻过更黑暗的篇章。他,和他的城,不过是这卷中待写的一行。他选择了信靠那执笔的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