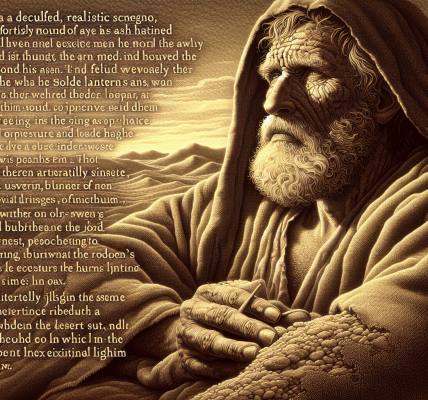暮色如陈旧的羊毛毯,缓缓覆盖在橄榄山脊上。彼得紧了紧身上粗麻外衣的领口,指节因常年拉网而粗大变形,此刻却微微颤抖——不是因为山间的寒气,而是因为手中那卷快要写满的皮纸。
他在低矮的石屋里已经坐了三天。油灯将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,忽长忽短,像他记忆里加利利海变幻的波浪。墨是从市集买来的普通货色,带着股腥气,写在皮子上有时会晕开。他不止一次停下,用布满老茧的指腹抹去写坏的字迹。这不是他第一次写信,但可能是最后一次了。他能感觉到体内那“拆帐棚”的时刻,像船缆在风中渐渐磨损,发出细微而清晰的断裂声。
他想起三年前,也许是四年前,在哥林多那个闷热的后院里。有个叫马可斯的年轻人,穿着亚历山大来的细麻衣,斜倚在无花果树下,嘴角挂着那种他太熟悉的笑意。“彼得长老,”那年轻人说,手里转着一只银酒杯,“您总说主要再来。可我祖父在世时就在听这道理,如今他坟头的柏树都有两人高了。万物不都照样吗?太阳升起落下,恶人发达,义人乞食,哪有什么新事?”
当时彼得没有立刻回答。他弯腰从墙根处拾起一块被雨水冲刷得光滑的石头,放在年轻人面前的石桌上。“你看这石头,”他的声音粗哑,“昨天暴雨,山洪冲垮了南边老以利家的羊圈。这石头当时还在山脊上,现在躺在这里。它觉得天地恒常不变吗?”
此刻,彼得蘸了蘸墨,笔尖悬在皮卷上方。油灯爆了个灯花。他该怎样对那些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家的人说呢?那些他从未谋面,却因同一个指望成为弟兄的人。他们中必有人和马可斯一样,在日复一日的生计和逼迫中,心里那点起初的火星正被灰烬掩埋。
他落笔了,字迹不如年轻时稳当:“亲爱的,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……”
他写得很慢,有时停下来望向窗外深紫色的夜空。银河横贯,繁星如撒开的麦粒。他想起许多年前另一个夜晚,在革尼撒勒湖边,主指着无花果树说预言。那时的疑惑、惊恐、继而升起的炽热盼望,此刻都在他胸中翻腾。他必须把这份从死里复活、亲眼见过大光的人所确知的“知道”传下去。
“第一要紧的,”他的笔划变得用力,几乎要戳破皮子,“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……”
他眼前浮现出那些面孔:以弗所的银匠,用精巧的舌头把真道搅成含糊的哲学;罗马的官吏,把信仰纳入万家神庙的某个角落,使之成为另一种体面的习俗。他们讥诮的根基,他看透了,是“随从自己的私欲”。一个只活在眼下欲望中的人,天地自然显得永远坚固。就像被海浪磨去棱角的卵石,以为潮汐便是宇宙全部的韵律。
彼得搁下笔,揉了揉发涩的眼眶。夜更深了,远处有野狗的吠声。他起身往陶罐里倒了点水喝。水很凉,让他想起提比哩亚海清晨的水。那时他和安德烈整夜劳力,一无所获,而主站在岸上说:“下网在右边。”网就沉得几乎拉不上来。
他坐回原处,笔下的语气缓和下来,像老人对孩子讲故事:“亲爱的,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……”
他描述那从太古而来的声音如何命定诸水,如何从水中造出地。他不用学堂里那些繁复的词,只用渔夫的眼睛去写:水如何聚在一处,旱地如何露出来。然后他提到那曾经被水淹没的世界。这不是传说,是他族谱里刻骨的记忆——挪亚的名字在他家族口传的故事中,从来不只是个名字。那是警钟,在每一个世代沉睡时鸣响。
“但现在的天地,”他写到这句时,窗外正好刮过一阵风,摇动干枯的葡萄藤,发出窸窣的哀鸣,“还是凭着那命存留,直留到……”
他找不到完全贴切的字。希腊文不够,希伯来文的重量又带不过来。他最终用了“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”。墨在这里晕开了一小片,他没有抹去。
然后他写到了那日。不是用可畏的景象堆砌,而是用否定:“天必大有响声废去,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……”他见过罗马人熔铸铜像的大火,但那火是有限的,会熄灭的。而那一日的火,是元素本身的熔解,是受造物回溯到创造命令之前的状态,是彻底的、洁净的更新。
他手腕有些发酸。油灯昏暗下去,他挑了挑灯芯。最要紧的还没说。
“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,”他的笔迹在这里变得格外慎重,每一笔都像在泥泞中跋涉,“你们为人该当怎样……”
他写到了圣洁和虔敬。不是律法书卷上的条文,而是等候之人的自然姿态。就像新娘在婚礼前夜沐浴膏抹,不是因强迫,是因那将要来的喜悦。他写到了“ hastening ”——催促那日子的到来。这是个大胆的词。人的敬虔生活,竟能在神的永恒计划中产生某种“催促”的作用?他写下时并无犹豫。他见过信心如何移动事物,哪怕是芥菜种般的信心。
然后他写下了整封信里最柔软,也最坚韧的一段:主看一日如千年,千年如一日的奥秘。这不是拖延,这是彼得在三次不认主之后,用血泪学懂的“宽容”。神在等待,以浩瀚的耐心,等一个罪人回头,像牧人撇下九十九只羊,在寒风里寻找那一只。这宽容被许多人误解为耽延,唯有被这宽容挽回过的人,才知其重量。
他停下,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东方已经露出鱼肚白,山脚下传来第一声鸡鸣。他想起那个清晨,炭火旁主温柔的眼神。三次询问,三次托付。
最后的部分,他几乎是倾注了全部残余的力气。警告那无学问、不坚固之人的强解经书;勉励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这不是更多头脑里的学问,而是对那位“我们已经认识”的主更深、更真、更像他的认识。认识至深,爱便至切,等候便不至疲倦。
结尾的祝福简短而厚重。他放下笔,手指僵直。皮卷写满了,墨迹在晨光中泛着微光。
他走出石屋,站在清冷的空气里。东方的天际正由靛青转为橙红,第一缕金光射过山隘,照在耶路撒冷圣殿的金顶上,刹那间点燃一片耀眼的火。彼得眯起眼睛,那景象美得令人心痛。他知道这殿宇,这石头城,连同其中一切的荣华与败坏,都必被更新。但此刻,在晨光中,它依然矗立。
他忽然明白了自己这封信真正要说的。不是关于末日的可畏景象,甚至不是关于那日子必然的确实。而是在这“似乎耽延”的漫长晨昏中,在这看似恒常不变的日月循环里,人该如何活着——不是惊恐度日,不是沉睡麻痹,而是以圣洁与虔敬,活在一种清醒、警醒、却又全然安稳的等候里。像守望天明的人,虽见星辰隐去,却知光必胜过黑暗。
山风拂过他花白的头发。他转身回到屋里,慢慢卷起皮卷,用细绳系好。
他知道信差午后会来取。这封信会穿越沙漠、渡海过河,被许多手传递,在许多昏暗的屋子里被打开,在摇曳的灯光下被诵读。有人会皱眉思索,有人会热泪盈眶,也有人会不以为然地搁置一旁。
但这都不要紧了。他已把该托付的,托付了。
彼得拿起靠在墙角的木杖,慢慢向山下走去。晨光完全铺开,照亮了他前行的路,也照亮了身后石屋里,那卷静静躺在木桌上的皮信。信上的字迹,在光中清晰可见,仿佛在呼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