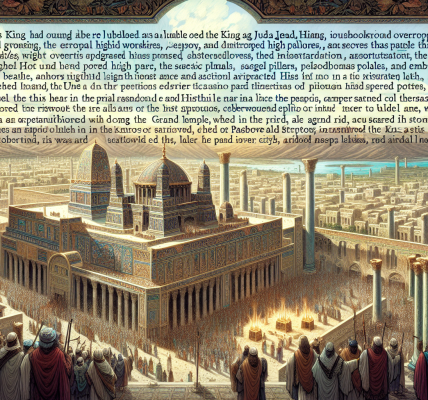正午的烈日把幔利平原的橡树林烤得发蔫,连蝉鸣都显得有气无力。亚伯拉罕坐在帐棚门口,皮革门帘卷起一半,热风像毯子一样裹着他九十九岁的身子。他眯着眼,看远处沙地上升腾起透明的热浪。
三个影子出现在路的尽头。
起初只是晃动的黑点,在蒸腾的热气里扭曲变形。亚伯拉罕用皱巴巴的手搭在眉骨上。他们走得不快,却转眼近了——近得能看见风尘仆仆的衣袍下摆,近得能辨出那是三个男人,却又说不出哪里让人觉得不同。不是商队,没有骆驼;不是游牧的族人,步态太过从容。有一种奇异的安静环绕着他们,连脚踩在碎石上的声音都被热风吞没了。
亚伯拉罕突然站起来,膝盖发出轻轻的声响。他掀开帐帘,几乎是跑着迎上去——那姿态不像个近百岁的老人,倒像个少年。他俯身在地,额头触到滚烫的沙土。
“我主,”他的声音沙哑,“我若在你眼前蒙恩,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。容我拿点水来,你们洗洗脚,在树下歇息歇息。我再拿一点饼来,你们可以加添心力,然后往前去。”
那站在中间的一位点了点头。他的眼睛像深夜的泉水,平静却深不见底。“就照你说的行吧。”
亚伯拉罕急忙进帐棚找撒拉。她正坐在织机前,梭子停在半空。“快,”他压低声音,却压不住那份急迫,“拿三细亚细面调匀,做饼。”撒拉没多问,只是看见丈夫眼里那种光——那种几十年前在哈兰,神第一次呼唤他时就亮起的光。她拍掉手上的线头,起身去揉面。
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,挑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,交给仆人去预备。他亲自取出奶酪和奶,摆在树荫下粗木拼成的矮桌上。橡树的影子慢慢移动,漏下碎金般的光斑。
他们坐在树下。亚伯拉罕站着侍立,像个仆人。风忽然转了向,从炎热干燥变得隐约带着凉意,从西方,从海的方向吹来。
“你妻子撒拉在哪里?”中间的那位问。
“在帐棚里。”亚伯拉罕说。他听见自己心跳得很响。
那人说:“到明年这时候,我必要回到你这里;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”
帐棚的厚毡后面传来极轻的、压抑不住的一声笑。像是被呛到的气音,又像是一声叹息。撒拉赶紧捂住嘴,但已经晚了。她老了,月经早已断绝,亚伯拉罕的身体也如同已死——这话实在太好笑,又好笑得让人想哭。
“撒拉为什么笑?”那人问,他的目光似乎穿透了厚厚的羊毛毡,“说:‘我既已衰败,岂能真有这喜事呢?’”
撒拉慌慌张张掀开帐帘出来,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“我没有笑。”她说。可声音虚得连自己都不信。
那人平静地看着她:“不然,你实在笑了。”
沉默突然变得很沉。奶酪在陶碗里慢慢融化,牛犊肉的香气混着烤饼的麦香,在奇异的凉风里飘散。亚伯拉罕看看撒拉,又看看客人。他想起许多年前在迦南地,神应许他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这些年,这应许像一颗埋在干旱地里的种子,他几乎要忘记它还在那里。
三人站起来,拍拍衣袍上的草屑。他们朝所多玛的方向望。亚伯拉罕也跟着望——平原的那头,城市在日光下泛着白色的光,看起来平静无辜。
“我所要做的事,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?”中间的那位自言自语般说。然后他转向亚伯拉罕,声音里有一种沉甸甸的重量:“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罪恶甚重,声闻于我。我现在要下去,察看他们所行的,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么?”
亚伯拉罕忽然明白了。他送他们慢慢往前走,一直送到可以俯瞰约旦河全平原的高处。另外两人先一步往所多玛去了,身影渐渐变小,最后消失在灼热的空气里。只剩那位还站着,等亚伯拉罕说话。
风完全凉下来了,吹得老人的胡须微微颤动。“无论善恶,你都要剿灭么?”亚伯拉罕问,声音很轻,“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,你还剿灭那地方么?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么?”
他们开始了一场奇怪的讨价还价。从五十个减到四十五个,到四十个,三十个,二十个,最后到十个。每减一次,亚伯拉罕的语气就更卑微一分,俯伏在地,像在悬崖边上拉住什么即将坠落的东西。“求主不要动怒,容我再说这一次……”
那人最后一次应允:“为这十个的缘故,我也不毁灭那城。”
说完,他就走了。亚伯拉罕独自站在高岗上,看着所多玛的方向。平原上的城市在暮色里升起炊烟,一切如常。他慢慢走回帐棚,脚步又变回九十九岁老人的步子。撒拉在门口等他,手里还沾着面粉。
“他们走了?”她问。
亚伯拉罕点点头。他握住她的手——那双曾经柔软、如今布满皱纹和裂口的手。“撒拉,”他说,“明年这时候,我们要有一个儿子了。”
撒拉这次没有笑。她看着丈夫的眼睛,看了很久。然后她说:“饼还有剩的,我热一热,你吃点。”
夜幕彻底落下,旷野的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,又密又多,像极了许多年前神指给他看的那片天。帐棚里亮起微弱的油灯光。远处,所多玛的灯火也亮着,浑然不知自己正在天平上摇晃。而亚伯拉罕和撒拉坐在橡树下,吃着凉了又热的饼,谁也不说话,只是偶尔抬头看看星空,又看看彼此,仿佛在确认一个太过美好而不敢轻信的梦。